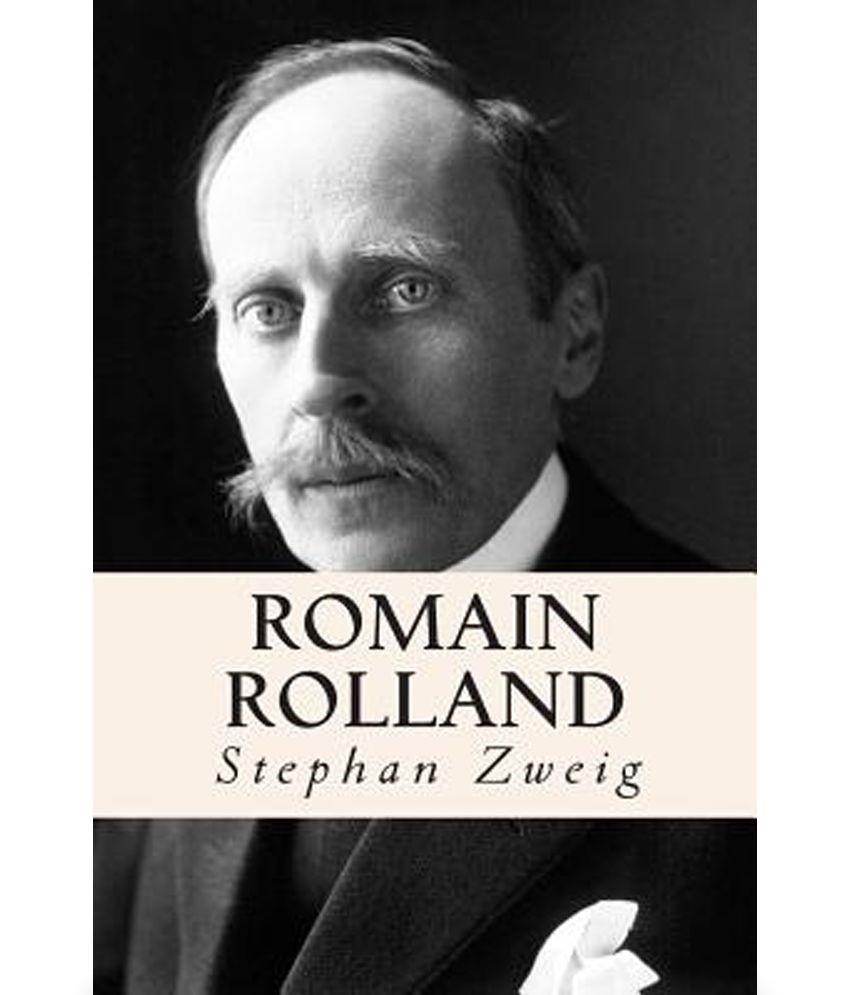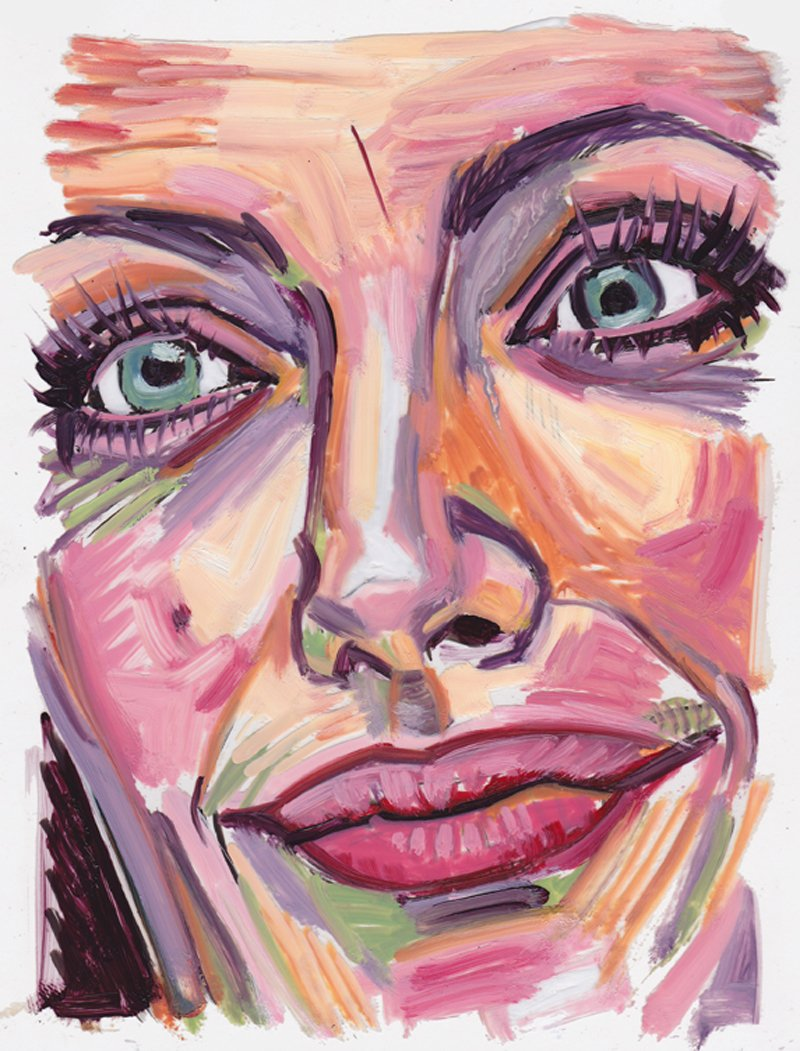在一杯咖啡中讀書寫字傾聽靈魂的聲音
李少詠(小木匠) 2022/02/09刊
世界如果沉睡了,有誰,能夠以什麼方式去喚醒她?
生活在這個擁有著龐大的近八十億人口的地球上,這也許是我們每一個讀過一點書的人(無論種族膚色士庶男女達官貴族還是引車賣漿者流)都有可能在某一段時間或者只是某一個短暫的瞬間思考過糾結過的問題。
我沒有想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有學習莊周老夫子筆下的那位自以為聰明的智叟,給出一個自己的答案哄哄自己,當然也有可能哄了一些實際上和我一樣自以為讀過幾本書的朋友們。我的答案其實很簡單,既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那就不去解決就是,只去做一件事:停下來,做思考狀,然後,告訴自己,為了自己內心的安寧,就拿起手中的鉛筆、鋼筆、圓珠筆、羽毛筆還有狼毫毛筆什麼的,以血為墨以大地作紙,描畫出蜷縮在這個世界某一個毫不起眼的角落裡的自己眼裡純粹的色彩和自己靈魂中毫不變形的聲音。
一
法國二十世紀著名哲學家埃曼紐爾·勒維納斯(E. Levinas, 1906—1995)曾經從存在的思考出發,打開了一扇存在的秘密之門。他把哲學與基督教、猶太教教義融會貫通,構建了一種“為他人”的倫理哲學;面對世上的邪惡、殘暴,勒維納斯要把現代人——不知自己生活在廢墟或者火山口上的存在,從政治昏睡、從江湖騙子的美夢及諾言中喚醒。他在自己的哲學名著《困難的自由》一書中說:“法蘭西使人發現她是這樣一個民族,人們可以憑藉精神與情感—-猶如憑藉種族歸屬於她。”
而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來看,勒維納斯所謂的精神與情感,在很多時候是可以置換為顏色與聲音的,那些從或簡潔或繁複的色彩中透射出來的聲音,使我們能夠從遠方感受到它的靈魂,幽雅玄遠而又溫暖濕潤。比如盧梭的聲音,比如巴爾扎克的還有雨果以及提著腦袋走上法蘭西學院神聖殿堂上拼死挽救一位黑人上尉的生命從而也為現代知識份子正名的愛彌兒·左拉的聲音。換句話說,我在很多時候是從顏色或者聲音裡感受那個遙遠而神秘的法蘭西的。那些聽起來很別致的聲音,會讓你如同中了魔法一樣不能自已。
在十八世紀法國神父卡斯代爾看來,聲音的特性是流逝,逃逸,永遠同時間繫在一起,並且依附著運動……顏色從屬於地點,它像地點那樣是固定的,持久的。它在靜穆中閃爍。
阻止我們由專制世界向自由之境逃逸的是從四面八方圍攏上來的黑暗。更確切地說是來自黑暗的聲音也即黑暗自身——一種空虛庸俗的窒悶力量。
為了我們的未來,我們選擇語言作為最後的武器,投入我們認為的理想世界的創造過程中。因為我們知道,語言是一種揭示世界,讓世界重獲人性的媒體。我們創造出屬於我們自己的語言,然後,從中得到我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無法得到的精神純潔,從而也在無意中完成了一次壯舉——對於正在瀕臨崩潰的世界的救贖。
二
如果一個作家的情感在立志改變世界的同時不與冷靜客觀相結合,文學對他將不再有所期待。文學知道,他所面臨的唯一機會就是在一個分支繁多的改變世界的過程中成為派生的產物。(瓦爾特·本雅明語)精神價值產生於其壓倒一切的力量和純潔之中。要注重作品的命運、當代人對作品的接受、作品的翻譯情況及作品的榮譽。這樣,作品便能夠在心靈深處構成一個微觀宇宙,乃至微觀永恆。因為,不是要把文學作品與它們的時代聯繫起來看,而是要與它們的產生,即它們被認識的時代——也就是我們的時代——聯繫起來看。這樣,文學才能成為歷史的有機載體。使文學藝術成為歷史的機體,而不是史學的素材庫,乃是文學史的任務。最佳的思考者的標誌就是:對時代完全不抱幻想,同時又毫無保留的認同這一時代。
咖啡是溫馨的有時候也是熱烈的。輕緩啜飲一杯咖啡,讓思緒浸潤在溫馨氤氳的清香與苦澀中,我們也許會有點驚喜地發現,那些不知不覺中裸露出來的靈魂是美麗的,那些聖潔的靈魂以文字凝成聲音,以這文字的聲音穿越世俗的時空直達人類靈魂深處,把靈魂中最隱秘也是最奇幻美麗的地方展示給每一個閱讀它們的人,讓所有閱讀者都從中找到自我,從而放任心靈的遊弋,在有限的生命和永恆的存在之間找到那個可以安然靜謐地享受生命的宴饗的內在支點,以此為土壤也為營養,在自己內心深處,培育出獨屬於自己也屬於整個人類的最燦爛的生命花朵,這是所有優秀的文字和畫面最值得我們珍視的地方。
中國漢文化傳統是由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共同構成的:其一是以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為基礎的殷商文化傳統,其二是以周滅殷之後建立的分封制國家為基礎的周文化傳統。前者是以上下等級森嚴的政治關係為主體的權力文化,後者是以家庭人倫關係為主體的人文文化。周之後,殷商文化傳統並沒有完全滅亡,只將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為中國漢文化統一的文化傳統根本無法說明中國文化發展演變的歷史。中國古代的儒學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其一是先秦從孔子、孟子到稷下學派的東夷儒學、山東儒學;其二是從董仲舒到韓愈再到二程(程顥、程頤)的中原儒學;其三是以朱熹為代表的南方儒學。東夷儒學是獨立知識份子階層的儒學,是以獨立知識份子的願望改善社會政治關係的儒學;中原儒學實際是以維護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政權為目的的官僚知識份子的儒學,從文化傳統的意義上來說,中原儒學實際是被斬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種換頭術,是以周文化為頭顱的殷商文化傳統,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種將政治專制與文化專制結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權力文化;南方文化則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整個上層社會的文化,與經濟的結合則是南方儒學的主要特徵,這為現代新儒學與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結合奠定了基礎。
三
保羅·利科在《言語的力量:科學與詩歌》一文中談到:“我完全同意感情就是詩歌言論所表達的東西。但感情是什麼呢?感情是一個確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問題。如果感情在詩中,它就不在靈魂裡。每一種感情都描述一種確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方向的方式。因而,說一首詩創造或引起了一種感情,是說它創造或引起了一種發現和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中的一種新的方式。……沒有什麼比感情更具有本體論性質。正是憑著感情,我們才居住在這個世界上。”
誰在靈魂中經歷過生死的冒險,而不是在直觀的哲理中將昇華當作逃避?我面前,站著你們;我的身旁,無數的男人女人已經走過或正在走過;而我的背後,是有如我的命運一樣鼓動著翅膀的想像,它撫慰或抽打我,驅逐我無目的的走去……
就像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中那個在純粹的被動中散發著原始的單一氣息的愛塔,是所有真正的男人的渴望與夢想。因為有了愛塔,那騷動不安的靈魂終於發現自己已經在那個純粹的男人斯特裡克蘭德身上找到了一個可以棲息的軀殼。
他是那樣地渴望潔淨,渴望一種靈魂把肉體甩脫掉的感覺、一種精神脫離形體的感覺。在那一刹那,他好像一伸手就能觸摸到美。“美在想像中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撫摸得到的實體。但他卻不得不拖著滿腳的污泥,甚至常常不得不躺在爛泥塘裡翻滾——他也許能夠讓你躲避家庭、愛情,無論是名義上的,或是事實上的,卻不能躲避自己肉體的衝動著的欲望。正是這種擺脫不掉的需要才使他對潔淨的渴望變得瘋狂。
而現在,愛塔站在他的面前。她是從塔希提島彌漫著燦爛的陽光、清新的空氣以及椰子樹、榕樹、火焰花、鱷梨花香的醉人的神奇誘惑中走出來的。她是女人。但更是有形的原始的氛圍,是一片野性的稚拙的大自然,那樣地牽動著他童年的夢想。
斯特裡克蘭德如此,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還有張承志《心靈史》的哲合忍耶人物群體,甚至最近改編成電視連續劇《上陽賦》的網路小說《帝王業》的主人公蕭綦、《天行健》的主人公之一楚休紅也是如此。在許多真正優秀的作家筆下,常常會有一個個追求者的夢想被永恆地塗抹在了生存和死亡的背景上。在每一個逝去的瞬間,它逼視著你飄忽而來,又轉眼消失得無影無蹤,一直遁入你的心底。那是宇宙初創時的圖景,是既崇高又冷漠、既美麗又殘忍的大自然本身,是無限的空間和永恆的時間,是一個巨大的誘惑,美得驚人又污穢邪惡……一句話,是一個浸透著痛苦意識的“自我”把握到的伊甸園、亞當和夏娃。
在文明發展史上,無論男女的兩性關係怎麼變化,只要不是社會物化了的,就一定深藏著這原始結合形式的種子。文化氣質的滲透,不是它的萎縮,不是背離原始性的單純的社會化趨向的發展,而是一種轉化著的、現時歷史的生命時間的注入。
在生命感覺的全面吻合中——男人說:你整個是為我的精神而存在,你是我的精神的載體,精神可以自由地出入,融合,或抽身而去。於是女人無言地迎上,連同精神一切升騰。
四
有一類作家藝術家,非有愛的對象不能萌發創造的衝動,善於把愛的對象和自己內心對美的追求混為一體,使性本能直接訴諸愛的形式,使自身和物件同時昇華為美,愛這個環節似乎成了目的本身,愛就是美。
能真實地愛也是一種美。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川端康成、高更、勞倫斯、梵古、徐青藤、弘一法師就是這樣的作家藝術家。
在這個世界上,又有多少人的生活閃耀過真正的愛,閃耀過結晶般的、一塵不染的美呢?俗世的現實中沾滿了世俗的污穢。
這個世界上又有多少人在常態的、死水一般的生活中活著啊。這是一種沉淪。純粹的、沒有任何期待和冒險的沉淪本身就是活著的死亡。而連在回憶和想像中都失去自由的沉淪,就更是一種活著的死亡了。
梅特林克說:“我們相知不深,因為我不曾與你同在寂靜之中。”語言,意義,我能與你同在這樣一種寂靜之中相遇相知嗎?
又想起了李叔同,那個還不叫弘一法師的清瘦的年輕人,當然還有他留給我們的那首永遠也不會變色走調的《送別》。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人生難得是歡聚,
唯有別離多。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問君此去幾時還,
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酒盡餘歡,
今宵別夢寒。
這首歌,就是一杯濃濃的咖啡。
一杯咖啡冷了,總有另一杯咖啡在火爐上沸騰,那樣我們都可以在咖啡的濃香裡見證天荒地老。它也許只是存在於我們每天的即溶咖啡裡——平淡到無味無聊無趣,卻親切到可以每天觸摸。
能夠欣賞甚至創造出那些以純粹的色彩與旋律描繪融合而成的靈魂的聲音,作為一個相信理想與未來,永遠對文學藝術懷揣夢想的讀書寫字的人,夫復何求?
作者:李少詠,自號小木匠,逍遙鎮人。能熬胡辣湯,會做粗陋的小桌子小板凳。喜歡讀書寫字,希望以此抗拒生命中的佞戾、虛妄與迷惘,都是半瓶子醬油水準。一生不敢或忘少年時代做木匠學徒時候師傅的一句話:想做一個好木匠,就不能用一根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