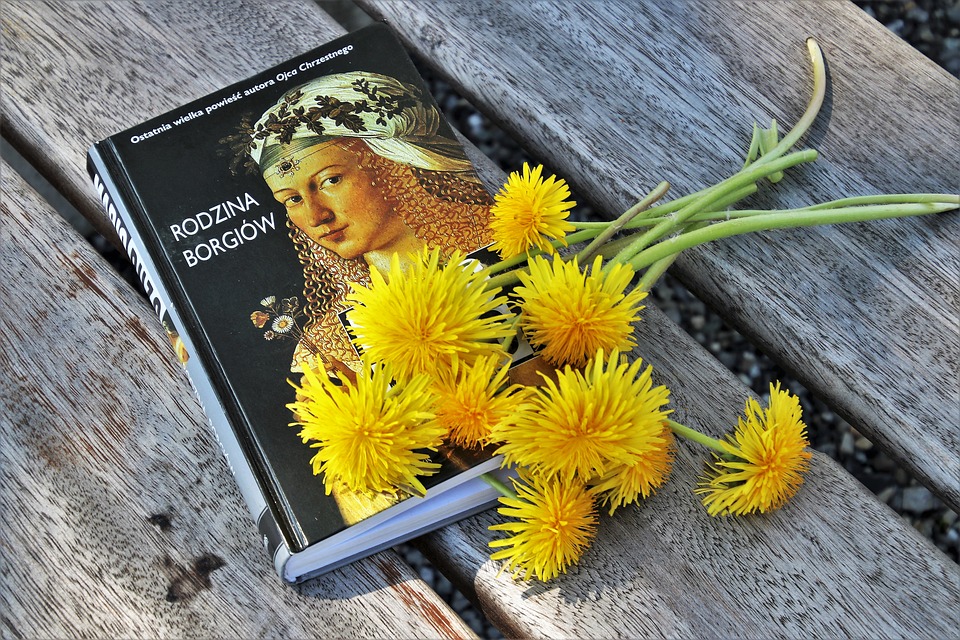莊學與會直立行走的小狗莊莊的因緣際會(李少詠)
李少詠 2021/10/10
一
當代最負盛名的文化批評家之一愛德華·W·薩義德在其《知識份子論》一書中說過,所謂現代知識份子,就是那些「以代表藝術(the art of representing )為業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具體一點說,現代知識份子就是那些「有能力向公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就這樣的意義上說,那些教授、博士、工程師、研究員們因其所從事的教學、設計、創造、研究工作同樣是人類外在技藝和內在精神的共同顯現形式之一,而當之無愧地可以稱之為現代知識份子。因為他們是一群真正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社會改造和人類自由解放,致力於淨化和美化人類的整個生活的理想主義者,也是以自己的整個生命作度世方舟,引渡一代代年輕的求知者順利走向美好未來,使他們的生命價值同樣得到最完美的實現的社會的靈魂奉獻者。而就現實的意義上說,他們不僅以自己的獨特的存在,代表了人類精神高度的現在,而且以他們的創造性工作,向我們昭示了我們這個世界的美好的未來。
莊學先生的小小說創作給我留下最深印象,或者說最打動我比較挑剔的閱讀神經的地方,不是它們精緻的敘事技巧,也不是個性鮮明的夾河灘語言風格,而是足以支撐起一份骨架淩然、底蘊沉厚的藝術世界的精神向度與審美特質。
簡而言之,莊學小小說讓他從龐大的中國小小說寫作者隊伍中越眾而出獨佔一座山頭的秘密武器,是他的小小說結構有骨架,人物有靈魂,獨特的精神向度與審美特質,是這兩者形成的玄妙法門。
換句更通俗一點的話說,莊學在寫作他的小小說作品的時候,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寫手,他還是一位凝結了一位現代知識份子精神基因的小小說創作者。
毋庸諱言,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我們都有可能不時的聽到一些感歎,感歎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太多的冷漠與無聊,太多的陰鬱與傷痛。我想,這正是我們無意中失去了對於美好未來的渴望與夢想。而在那些優秀的作家藝術家筆下、口中和指尖兒上,我們幾乎是無一例外,都能夠隱隱約約的看到一張張藝術家或者是現代知識份子的模糊的面容,在那一副副不同的面容上,我們還能夠看到一抹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顏色,那是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哈佛大學教授羅爾斯先生所極力推崇的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顏色——羞色。從那一抹抹羞色掩映下的笑容與沉思中,我們也能夠一次次看到某種渴望與夢想。那種渴望與夢想,是閃爍在我們生活上空的那一抹絕世美麗的雨後輕虹,是縈繞在我們心靈深處的那一絲隨風起舞的玄妙梵音。它們使哪怕一顆最平凡的靈魂也不能容忍世間的自私與卑怯,庸俗與無聊,欺詐與苟且;它們更使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一份純淨的心地明朗的樂觀,因而敢於直面任何困難與挫折、失敗與屈辱。某種意義上說,擁有了一份美麗的渴望與夢想,也就是擁有了一份前行的永恆動力,擁有了一份生活幸福和快樂的切實保障,也從而讓我們的生命擁有了一種永遠不會褪色的燦爛與輝煌!我們的生命之花將因為有了它們而更加鮮豔,我們的創造力量將因為有了它們而永不枯竭,我們的靈魂之歌也將因為有了它們而永遠高亢、明亮!
那是精神的力量,面對它,感悟它,我們有時候會不由自主的想起自己的故鄉。故鄉是一個包納廣泛,極具象徵和精神意義的詞彙。故鄉生髮和保存的文化符號、風土民俗、鄉約精神等,會成為我們每一個人一生最基本的行為法度,最珍貴的人格品質,仿佛河流、高山或醒目的碑匾,不止指引和決定著我們的生命成長軌跡,影響著我們的氣質秉性,同時對我們的邏輯思維、認知現實的能力以及寫作方式和內容,都產生著不可撼動的影響。
比起來,作家對故鄉變遷之體味察覺,以及對故鄉風物人情的感受,要優於其他行業者,所以文字中呈現出來的故鄉,也要比其他領域呈現出的更加寬闊、宏大,更加細緻、美好,更加全面、準確。
以故鄉或地域為源頭,從此流向廣闊山河蒼茫大地的寫作比比皆是,而故鄉卻是很多作家寫作時候隨身攜帶的精神行囊。如瑪律克斯的馬孔多,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沈從文的湘西,蘇童的楓楊樹,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等等,而莊學擁有的是他的伊洛河交匯之處的夾河灘。
他很好地運用了故鄉夾河灘在社會發輾轉型時期的時代背景,使文本的呈現,具有一種獨屬於他和故鄉的氣韻。
在閱讀莊學先生小小說的過程中,頭腦裡一個意念曾經於不經意間悄然萌生並且越來越清晰:
莊學先生是在小小說創作過程中悄悄建構一個由夢想甚至還可以不客氣地說是野心促生的精神或者審美的殿堂,那座殿堂裡只有一盞燈在閃閃爍爍迷亂著我們的目光也迷亂著我們的心靈,那盞燈就是那一句話:
站立起來!
二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
當高更在那個充滿著蠻荒而神秘意味的塔希提小島上孤獨而蒼茫的發出這千古一問的時候,我們人類的生命之舟已經飄搖在歷史與現實交匯處的一片汪洋大海上。我們開始希冀更好更清醒地認識我們自己。走出家門的渴望就從那時開始萌生。我們已經意識到:當還在母親身邊學著走路的時候,作為本質意義上的我們就還沒有哲學意義上的誕生。我們的兩隻笨拙的小腳在家的外面拌在石頭上時發出的第一聲呼喊,才是真正人本意義上的我們降臨人世後的呼喊。沒有家鄉的無邊曠野,沒有家的堅固四壁保護我們的地方,才是考驗我們性格品質之場所。而我們走出家門的前提,當然首先是要站立起來。
站立起來,是人類由嬰兒時代向成長為人過渡的第一個關鍵時刻,只有站立起來了,我們才能走路,走很長的人生之路,走的不好的,很快跌倒,走得好的,無遠弗屆。
文學比國家更恒久,它以語言訴諸記憶,進而戰勝時間和死亡;人類面臨每一次精神危機的時候,總有文學站出來,撫慰人們的心靈,激勵人們的鬥志,重新燃起人類對於美好未來的希望。在先秦,它是中華智慧源頭的諸子百家散文;在唐宋時代,它是光耀千秋的唐詩宋詞;元明清以來,雜劇、戲曲和小說佔據了最為引人注目的位置。它們所構成的,正是人類精神和藝術發展史上極其輝煌燦爛的一片片美麗的星空!
在物質力量越來越強勢的決定世界結構和社會關係的外部現實領域,已經越來越強大了的世俗文明之流中,尋求和確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直是現代有識之士不遺餘力,甚至不惜生死一之的努力方向。他們追尋的結果之一,是認定人類要想真正的走向現代,必須竭盡全力打造好生命的精神基礎,在這一認知觀念之下,認定高尚、超越性、精神價值,是人的本質的決定性特徵。而熱的精神性之外存在的世俗的絕對權威,在認定現代性進程中反而會自覺不自覺的成為一種阻礙或者桎梏,只有不斷沖決和打破這一桎梏,以特殊的方式走近人的精神世界,學會從精神深處、從內向外認識自己也認識這個世界,才能有效的一步步走向現代性的理想未來。因為他們深切認識到,人的外部生命存在形式和社會組織形式的本原基礎,不在外界而在內心,在人的精神深處。不是強力和物質秩序決定一切,而是精神信仰和物質秩序的有機融合,才能夠成為人類走向自由富足和思想現代化的基礎和源泉。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以堅韌不拔的超卓努力,最大可能的擺脫那些控制了我們的精神,讓我們陷入心理的世俗化與靈魂的粗鄙化的泥淖的東西。
在我的閱讀視界中,還沒有發現一個人,沒有發現一個作家在他們的生活和創作過程中,不懷有站立起來,走出家門,重建純潔美麗靈性十足的生命家園的渴望。
我們知道,我們通常情況下的寫作總是傾向於有所斷言的,它習慣於使用一種硬化的、封閉的,排除歧義的語言,它從未想賦予語言、思想與寫作的延存以一系列變動的近似態,而是強行表現出一種在被說出以前就業已存在的言語現象。在這個意義上,寫作者或個體思想者自然也就成為了一個個支配性的,更高的精神或歷史價值的代言者,他們深信自己個人的思想與行動無非是實現歷史必然性的一個工具。《會直立行走的莊莊》展示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寫作者或個體思想者對於自己處身其中的生活環境進行形而上的改造的隱秘精神指向。
莊莊是條狗,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條男狗。在一個很多男人從某種精神意義的層面上來說,於不知不覺中已經被悄然抽去了精神脊柱,因而也無奈地失去了精神生殖力和創造力的生活氛圍中,這樣一條特立獨行的男狗出現在我們的閱讀視界中,顯然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通常情況下,狗,無論男狗還是女狗,是不會直立行走的,這是我們都知道一個生物學常識。而莊學先生卻偏偏讓他寵愛的男狗莊莊學會了直立行走,這一點已經先聲奪人,抓住了讀者渴望的或者是挑剔的眼球。
人是什麼?是高級智慧動物呀。人區別於低級動物的顯著標誌,那就是會直立行走,會產生思想,會想盡一切辦法控制對方,會貪婪地掠奪自然界萬物而唯人獨尊。人還會面對面地性交,並將性交說成是做愛。有專家說了,人的直立行走和面對面的性交是人類進化的重大基礎,由此而奠定了人類在地球上的主宰地位。所以人可以稱小貓小狗為寵物,而小貓小狗只會對人搖頭擺尾做出依人狀。
小說一開始就是這樣一串疑問和作者的議論,一般情況下,這是小說創作尤其是小小說創作的大忌,而就這個小說來說卻是作者的聰明所在。它以這樣的方式,直截了當地把作家對於人類生活和個體生命認知過程中的思考和困惑托出來,展現在了讀者的面前。它的精神指向,是通過展示一個人類主體性的一步步被泯滅的過程,揭示出潛藏在我們所有人精神心理內部的,對於人類主體性一點點被泯滅的源自靈魂深處的恐懼,當然還有對於解脫或者消除這種恐懼的靈魂深處潛藏著的殷切的渴望。
那種從靈魂深處迸發出來的殷切的渴望,類似於我們通常所說的神話力量的衍射物。《神話的力量》的作者約瑟夫·坎貝爾說過:「大家認為生命的意義就是人類所追求的一切,我並不這樣認為。我認為人類真正追求的是一種存在的體驗,因為這種體驗,我們一生的生活經驗才能和內心的存在感與現實感產生共鳴,我們才能真正體會到存在的喜悅。那就是生命,神話幫助我們發現內在自我的線索。」小狗莊莊的生命渴望和精神嚮往,正是這種類似於神話力量的影響與激發的產物。
三
英國神學家詹姆士·裡德認為,恐懼是我們人類生活中的一個永遠無法擺脫的東西,「許多恐懼都是來自我們對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理解,來自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控制。」因而「為了實現完滿的人生,需要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獲得控制恐懼的力量。」而巴斯卡則說得更為明白:真正的恐懼來自信念;虛假的恐懼來自疑慮。真正的恐懼是伴隨著希望的,因為它來源於信念,而且因為人們對自己所信仰的神抱著希望。虛假的恐懼伴隨著絕望,因為人們對自己所信仰的神懷著恐懼。前者怕失去神,後者怕找到神。
事實也的確如此,就人類思想史的維度上來看,人類對於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終極恐懼,常常是在一種並不自覺的狀態下突然產生的。這些恐懼之所以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左右甚或宰製人民尤其是那些有文化能思想的知識份子的身心,是因為它們既不是簡單的害怕,也不僅是一種個人情緒的釋放,而是直接切入我們的生存本源的。它們與我們人類的生存狀況、時代狀況、歷史傳統等等都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關聯。也正因為如此,人類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些知識精英們,總是一直在嘗試著要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創造或者建構一座知識的城堡供人們平安喜樂的享用。馬克思、恩格斯如此,列寧、史達林如此,魯迅先生也如此。
恐懼有時候會引發無聊,如存在主義鼻祖克爾凱郭爾所說,無聊這兩個字暗示我們一種分類的可能性;它能顯然指出兩種人:使人無聊的人和自己無聊的人。使人無聊的人是俗人,群眾,無窮無盡的庸人之群;那些自己無聊的人是智慧者,精神的貴族。並且那有多麼奇怪:自己不無聊的人,通常使旁人無聊,反而自己無聊的人,卻供旁人消遣。莊莊的行為,顯然是他主人「無聊」或者說「大智慧」的靈機一動的產物。它讓我更加感到了小說家與魯迅先生在某種靈魂生髮點上的莫名契合。
我一直認為,在魯迅先生的小說中,最具審美價值內涵的,往往不是其人物形象中的性格美,而是其人物角色話語或者行為中所裹挾的思想含量和技術含量。在魯迅小說的審美活動中,與其審人物的性格形象,不如審人物的思想形象;與其審人物形象的性格美,不如審人物形象的思想美。一句話:「顯示靈魂的深」才是魯迅小說詩學的最根本的特徵,正是這種文化詩學的特徵使得魯迅先生的小說成為了弗裡德里希·詹姆遜所言的具有典型的「社會象徵性行為特徵的文化製品」。
《會直立行走的莊莊》所展示給我們的,正是像魯迅先生小說所展示給我們的那樣一種直指人類靈魂最隱秘處的深刻,以及小狗莊莊與天鬥主人或模糊或清楚地感知到的莫名的恐懼。
小說敘事人「我」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把一隻普通的小狗莊莊,艱苦卓絕地訓練成為了一隻會直立行走的狗,然後不無驕傲地帶著莊莊走入了外面的世界,人類的世界。「莊莊的出現,馬上引起了人們的驚訝和羡慕:嘖,這狗是狗嗎?嘖嘖,真是一隻另類的狗啊!嘖嘖嘖……」
莊莊以直立行走的傲狗姿態贏得了其他狗們無法替代的驕傲的資本,「地上趴著的狗們集體向莊莊注視了三秒鐘」,請注意,是「注視了三秒鐘」!當然,還有一隻美麗的雪白的小母狗探索般地圍著莊莊轉了一圈,還在莊莊的肚肚下面嗅了嗅,這一點對於男狗莊莊極其重要。問題在後面,美麗的雪白的小母狗做完了那個親熱的動作之後,「馬上跑回了狗們的中間」。「狗們一哄而散,繼續著他們未競的遊戲。」
莊莊獨自站在那裡寂寞無比。
這才是和人類一樣能夠直立行走的小狗莊莊,或者說就是人類中的精英們的一種最深切的悲哀!
「莊莊想走到狗們中間,走到那只雪白的小母狗跟前。可是莊莊走到哪裡,狗們就逃離哪裡。直立行走的莊莊並不比四肢著地的同類跑得快。
寂寞的莊莊環顧四周,身子不由地顫抖起來。它剛想放下直立著的身子,看見我揮舞著的大骨頭,又趕緊把身子挺直了。”
我愉快而又自豪地向圍著我的人們介紹聰明的莊莊,傳授訓練莊莊的經驗。在我唾沫四濺的時候,人群外有人高叫:天哪!那只直立行走的狗呢?
我急忙扒拉開人群,只見莊莊四肢著地顛顛地奔向那只雪白而又美麗的小母狗,融入到了狗們的中間。
小說家莊學的聰明在這樣的結局描寫中顯露無遺。
直立行走,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精神向度,而最後的融入到群狗之中,則是獨立精神退回起點的標誌。小說最有意義的價值所在,是對於訓練一隻原本四肢著地的狗直立行走這樣一件事情的發現與展示。
四
剛剛頒發的202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由坦尚尼亞裔英國籍作家古爾納獲得。根據這兩天各種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有關介紹,古爾納的小說顯然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視野,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文化多元化的東非,這與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格和色彩。在古爾納的文學世界裡,一切都在變化——記憶、名字、身份。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一種受知識熱情驅使的無休止的探索,比如最新作品《來世》中,這種探索同樣突出,就和他21歲開始寫作時一樣。他還一直站在非洲的立場講述非洲的故事,關注坦尚尼亞人在異國他鄉的遭遇和處境。
古爾納的最新小說《來世》故事發生在20世紀初,也就是1919年德國對東非的殖民統治結束之前。故事主人公哈姆紮在一次德國士兵的內部衝突中受傷,被留在野戰醫院接受治療。但當他回到海邊的出生地時,卻既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留下了。
原本有的,突然沒有了。
這就是古爾納留給我們的精神啟示。莊學先生的小說,認真回想起來,同樣也在給予我們帶來一個個不同的精神啟示。
一直讓我念念不忘的《會直立行走的莊莊》當中,莊莊的遭遇,不是和古爾納的《來世》一樣,以形象化的手段,向我們提出來了一個足以振聾發聵的問題嗎?《拯救》、《兵爸爸》、《觸摸爸爸》、《掃街的女人》等篇什則是同樣是從不同的側面對於“成為獨立的、大寫的人”的精神追求的不同層面不同角度的回答。
《拯救》和《兵爸爸》是對於英雄主義的極具作家個性化特徵的藝術解析。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安德列·紀德說過:「一個人的實質,不在於他向你顯露的那一面,而在於他所不能向你顯露的那一面。因此,如果你想瞭解他,不要去聽他說出的話,而要去聽他的沒有說出的話。」這段話事實上是在告訴我們的小說家們,怎樣才能夠在小說中揭示出人類生活中那些最本質化的東西。那就是,要設身處地地深入小說人物內心隱秘處,把那些不能言宣或者主人公不願言宣出來的東西發掘並且展示出來。
《拯救》寫了一個由懦夫轉化為英雄的士兵和一個殘疾姑娘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很多作家都能寫出來,區別在於,有的作家能夠透過這樣的故事揭示出人性的本質,有的則只不過是隨隨便便的講出一個也許有點意思也許味同嚼蠟的故事而已。莊學這篇小小說,顯然是屬於揭示出了人性的本質特徵,並且因而能夠給讀者以較深刻的精神啟示的作品。
在突如其來的巨大自然災難面前,年輕士兵由於恐懼而不知所措,而退縮到安全的地方。從人性本質屬性來說,這種趨利避害的行為並沒有什麼不正常。然而,他是士兵,是戰士,這樣的身份就決定了他不應該這樣做而應該是沖到最危險的地方做一個救助者。矛盾由此而來。士兵在事情過後陷入了幾乎是無邊的悔恨與痛苦之中。而排長的犧牲更加重了這一內心自我懲處的力量。最後,他成為了一名通常意義上的捨命救人的英雄。
聰明的或者智慧的作家,往往善於把吸引、衝突、反差、轉變等元素巧妙運用于愛情、友誼、合作乃至任何類型的人物關係的創造過程中。在這一點上,莊學的創造性顯示的非常充分。
在莊學的筆下,懦夫轉化為英雄的士兵內心的痛悔被作家處理得很巧妙,不露聲色而張力無窮。女大學生的出現則自然而然沒有任何牽強和人為的痕跡。在痛悔和自責的夾縫中,女大學生悄然以一封信的形式出現在士兵的生活中,而且是經由犧牲了的排長而間接地出現的,這就有了深長的意味了。拯救,不僅是對於為難者的拯救,更重要的是對於自我的靈魂殘缺的拯救。女大學生的殘疾,從另外一個角度更加有力地強化了這種精神或者靈魂拯救的力度。也就是有了這樣的拯救,作家筆下的人物身上才顯露出了最可貴的人性光輝,讓他們自己作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獨立地站立了起來。
《觸摸爸爸》和《掃街的女人》一以側面烘托一以大筆直書的方式,同樣寫出了兩個站立起來了的人物。支撐他們站立起來的,同樣是理想主義照映下的人性的光輝。
不斷尋求生命價值和意義的突圍的理想主義精神,是莊學在他的小小說創作中秉持的最有力、最犀利的精神武器。就憑藉這一無往而不利的輝煌大殺器,他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為我們描畫出了一幅幅深含生命哲理的藝術圖景。
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德國思想家阿多諾在其對現代藝術史發展影響巨大的《美學理論》一書中,將精神提升到了人類生命和藝術創造本源一般重要的地位。他指出:「藝術作品的精神是其增值或盈餘……精神將藝術作品(物中之物)轉化為某種不僅僅是物質性的東西,同時僅憑藉保持其物性的方式,使藝術作品成為精神產品。……精神不只是灌注藝術作品以生氣的呼吸,能夠喚醒作為顯現現象的藝術作品,而且也是藝術作品藉此取得客觀化的內在力量。」因此,「如果不顯現出精神,或者說沒有精神,藝術作品也就不復存在。」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莊學小說作為優秀藝術作品的魅力充分展現了出來。具體來說,通過筆下千姿百態的作品,莊學向我們展示出了他從古老深厚的河洛歷史文化和大片大片的夾河灘風光中汲取的精神滋養,也因而把他自己作為一位優秀小說家的形象透射給了我們。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文知識份子的代表,他的小說,是他對於自己所處身其中的日常現實生活的最真實的摯愛和自我靈魂深處最強烈的對於人生本質價值和意義的深刻理解以及對於人類崇高理想追求的有效表達。
作者李少詠
李少詠(1965 —— )河南西華逍遙鎮人,教授,文學博士,先後任教於周口師院、洛陽師院。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洛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曾獲得河南省文學獎、河南青年作家獎、河南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發表有文藝評論、小說、詩歌、散文等三百餘萬字,有評論文字《沒有人看見草生長》《傾聽與闡釋》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