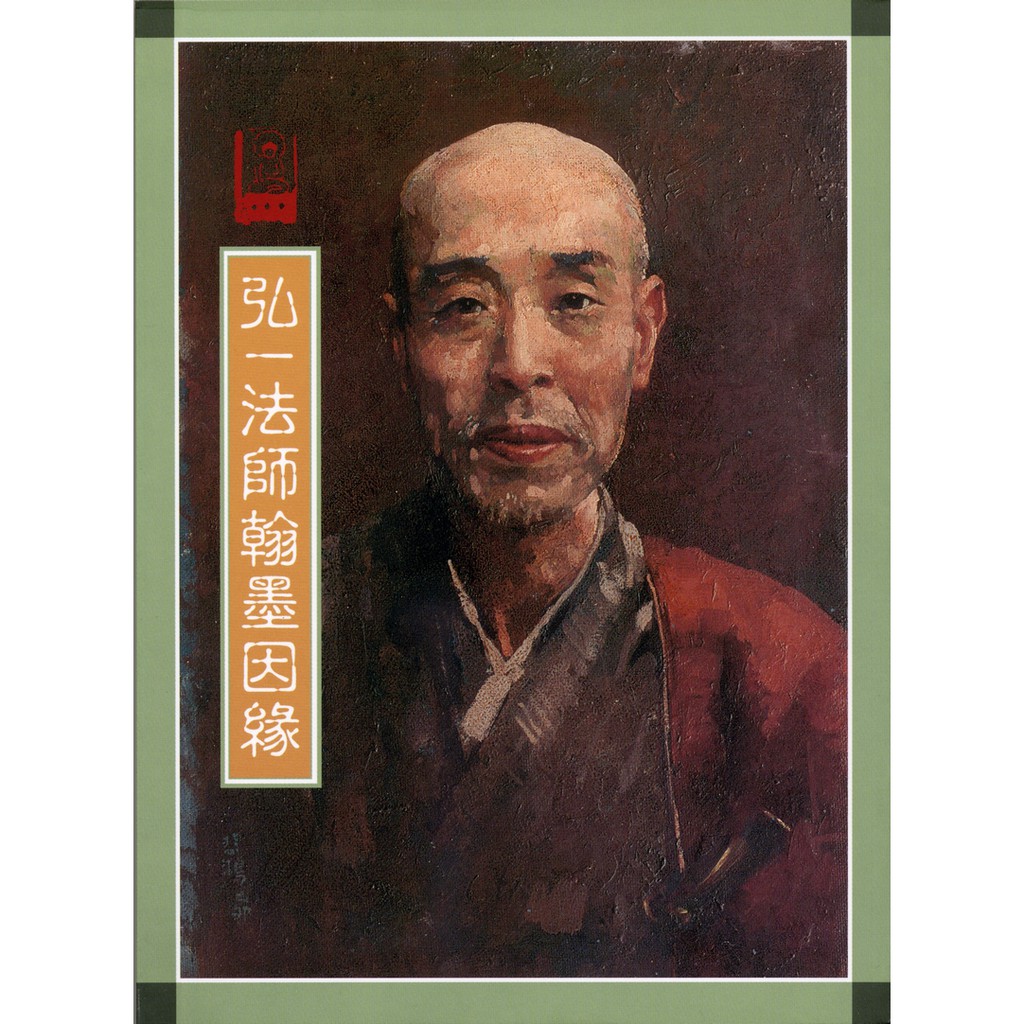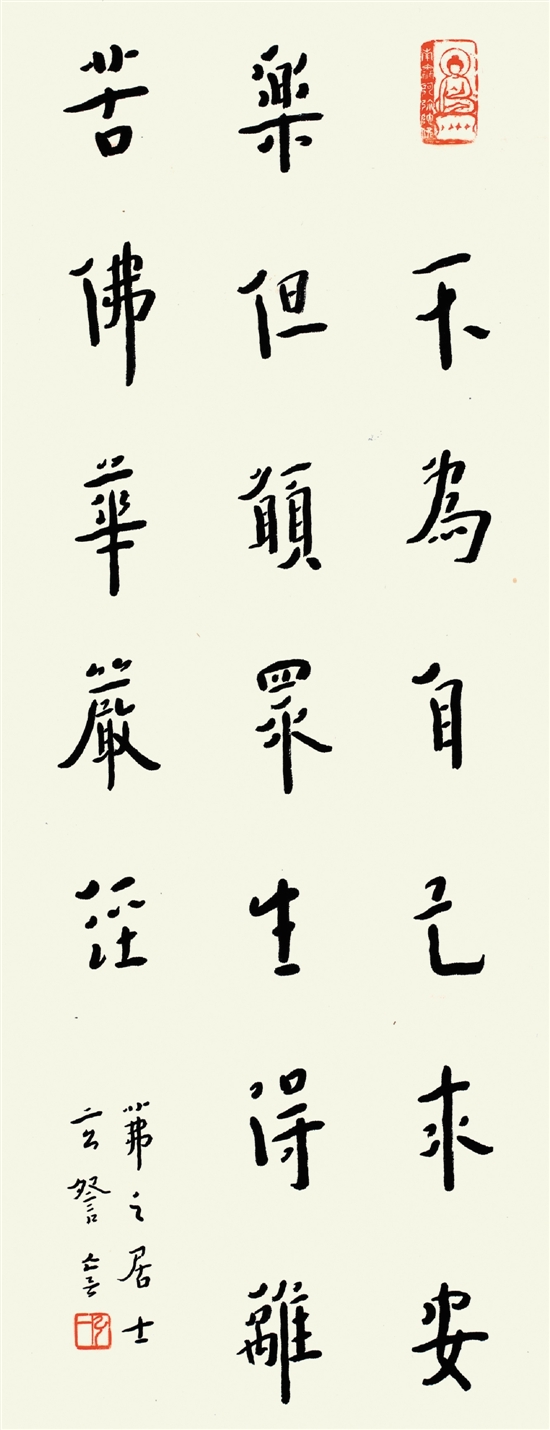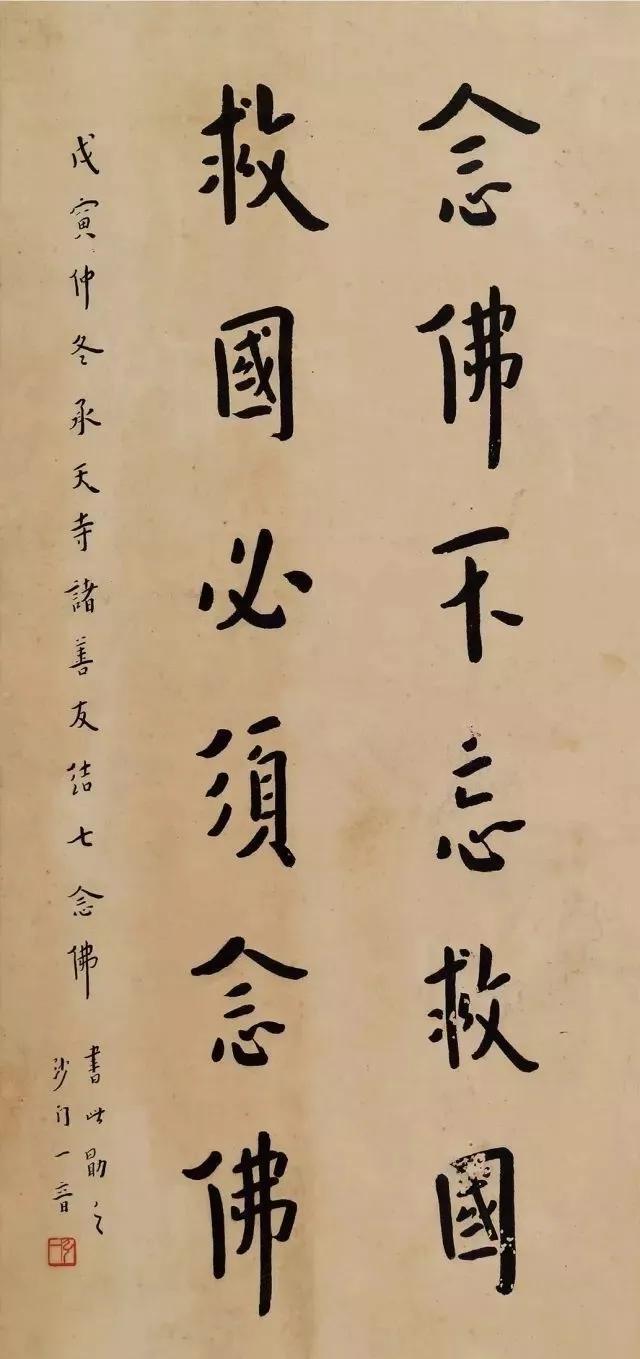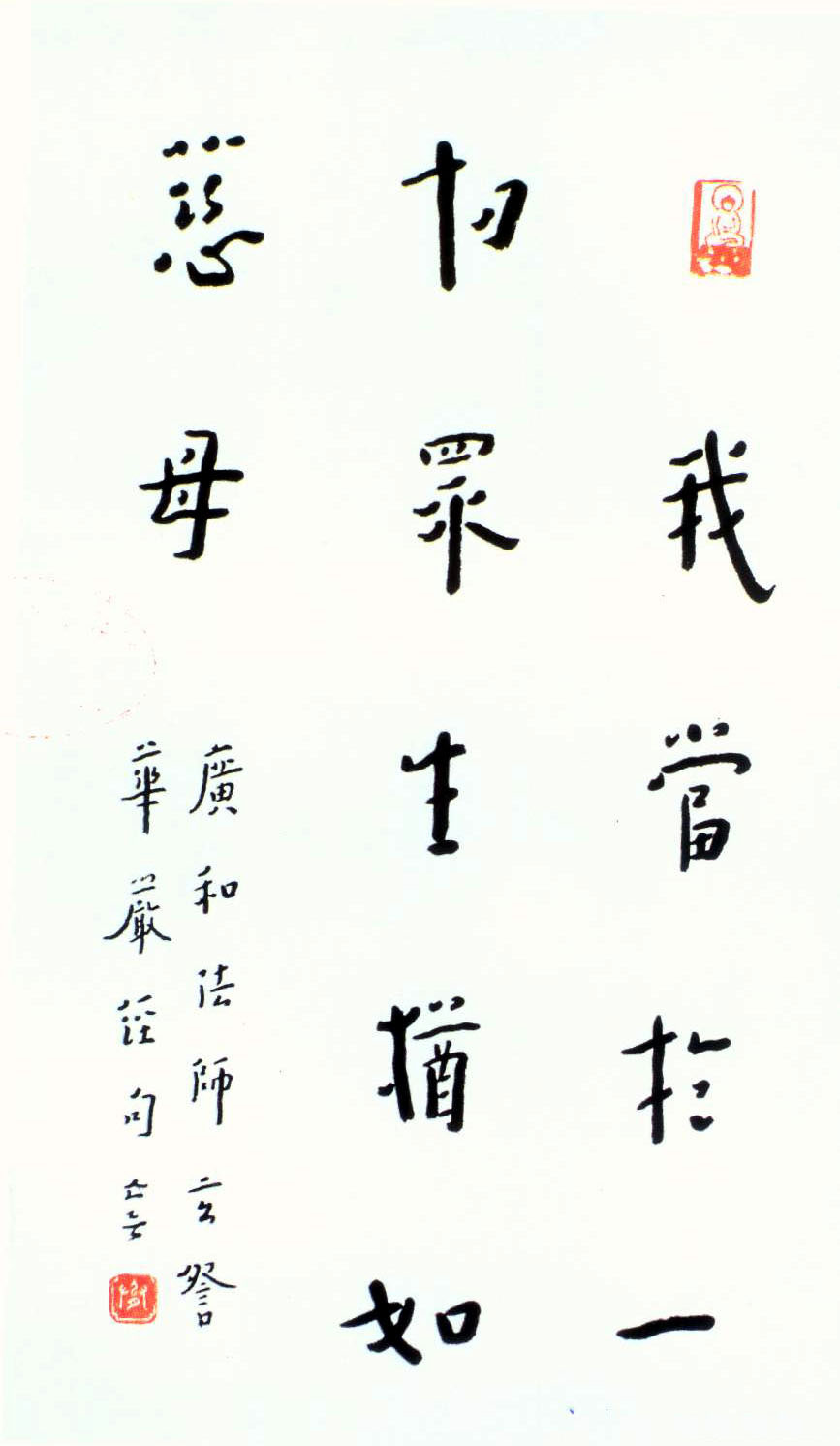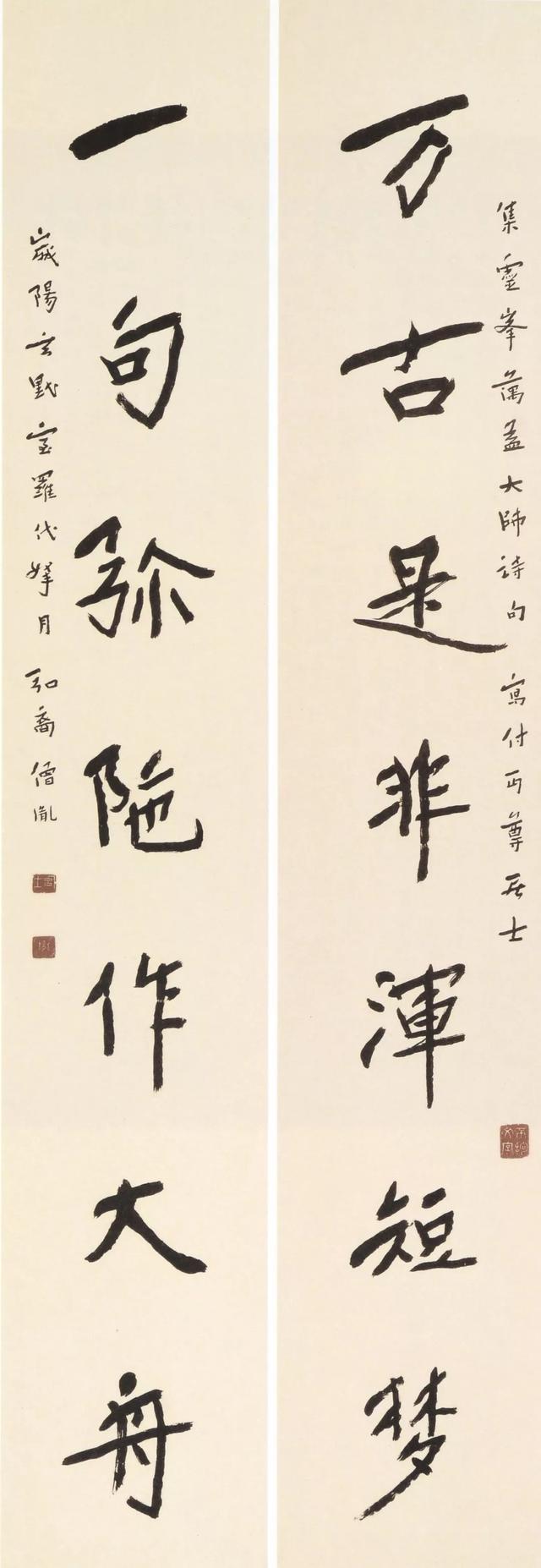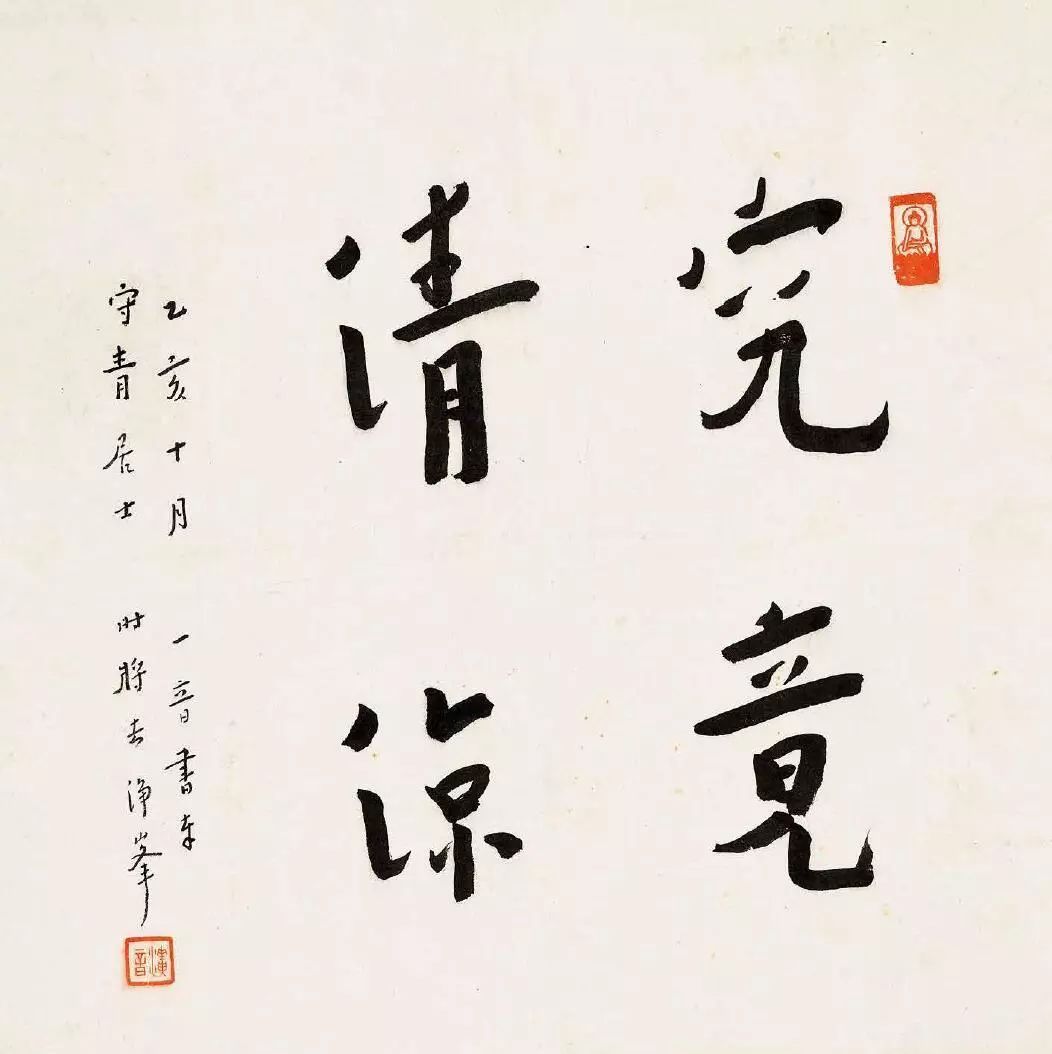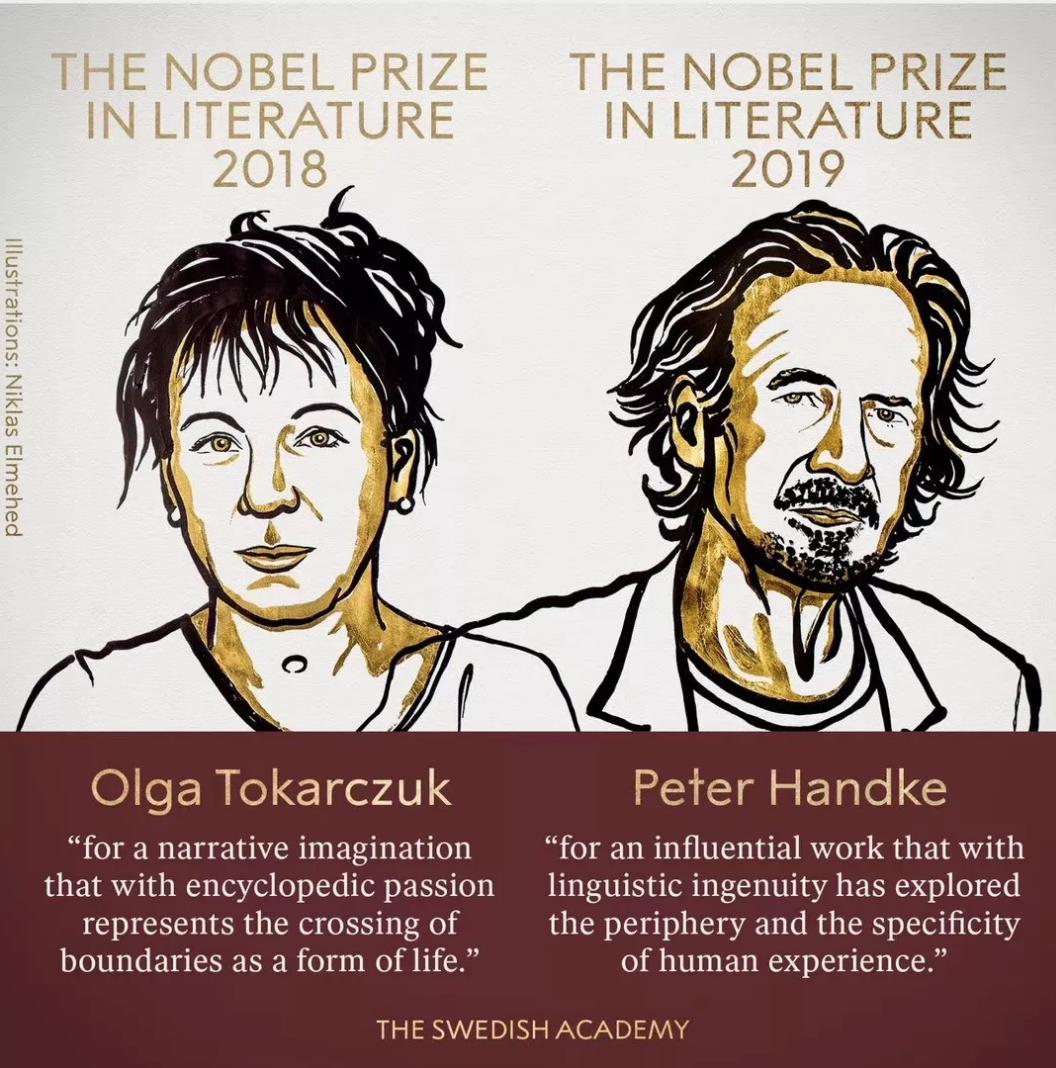為了更好的批評,先要認真的欣賞
李少詠(小木匠)2021/10/17
今天開始我和大家一起聊聊文學欣賞與文學批評。
什麼是欣賞?通俗一點說,欣賞就是喜歡。
就像一個人會喜歡另一個人,比如一個小夥子會喜歡一個姑娘,一個姑娘也會喜歡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小夥子,比如所謂的白馬王子或者黑馬紅馬花馬王子,這喜歡也就是欣賞了;喜歡的時間久了,就會希望走到一起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當然,走到一起是要有條件的,各種條件。批評或者說相互批評是走到一起後常常有的現象。
文學欣賞也是這樣,欣賞水準高了,層次深了,欣賞主體就會產生某種把自己的欣賞感受表達出來的願望,於是,文學批評出現了。文學批評是文學欣賞的高級形態。文學欣賞是戀愛階段,是面對的兩個人的世界,在兩個人心目中甚至只是一個人的世界,隨心所欲只管自己高興或者不高興,想到就說,百無禁忌;文學批評是結婚之後,有了更多的快樂,當然,也有了更多的責任與義務,也就是不能隨便說了。用術語來說呢:
所謂文學欣賞,就是運用自己的思維器官,對文學作品進行感受、體驗、想像和思索,從而獲得美的感染和愉悅,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它包含感受藝術形象,體味藝術境界,領會思想內容,激起情感反應,玩賞藝術魅力,鑒別作品品質等等,總之一大堆內容。
文學欣賞是我們人類和文學關係的初級階段,是基本形態,就像社會主義;它的高級形態或者說它的發展產品就是文學批評,它們是一體兩面的。它們合在一起,既是一種特殊的精神實踐活動,又是一種特殊的審美認識活動,大體說來,它具有四個方面的基本特徵:
一、文學欣賞是一種借助形象與感情的審美享受活動,它始終離不開藝術形象的誘導和強烈情感的激發。
一般來說,讀者在欣賞文學作品時,常常是首先被作品中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所吸引,所感染,引起情感上的強烈反應,然後才會深入其中比較全面的認識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現實面貌,並進而理解它的本質意義。所以說形象所喚起的欣賞者的情感反映,是審美享受的重要標誌,是文學欣賞的一個重要特點。例如:人們在欣賞《保衛延安》、《青春之歌》、《創業史》、《紅岩》等作品時,就會特別喜歡作品所表現的可歌可泣的鬥爭生活,喜愛那些鮮明生動的革命者的光輝形象。從作品中瞭解過去的革命鬥爭歷史,學習先輩的革命傳統與鬥爭精神,並陶冶自己的情操與堅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在閱讀高爾基的《海燕》、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等作品時,作品所展現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生活,以及從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堅強的革命戰士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時期,對廣大讀者都具有巨大的教育、鼓舞力量。這種感情上的反應是很強烈的。還有大家應該比我更熟悉的《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在詩三百當中,無論論語言的優美還是論境界的高妙誘人,恐怕都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的。我們讀它,吟唱它的時候,當然首先是感受那一份咱們的先祖們的純美情懷吧。還有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余光中的《鄉愁》,舒婷的《神女峰》等,都是裡面的情感先打動我們的啊。總之,欣賞者的情感反映,以文學作品的形象系統為基礎,以作家在作品中所灌注的情感為動力。
二、文學欣賞是感覺與理解相統一的審美認識活動,在欣賞過程中,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結伴而行。
文學欣賞不是簡單地復現形象,而是對形象意蘊的深刻理解。這種理解又不是抽象的認識,而是形象的意會,是在感覺中理解,在審美過程中認識。文學欣賞以讀者對作品中的藝術形象的具體感受為基礎,讀者對作品的感性認識,在文學欣賞中有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夠更深刻的感覺它」。讀者對文學作品的形象,只有在正確理解的基礎上,才能獲得深刻的感受。例如,宋代詩人蘇軾,在讀了陶淵明的《飲酒》詩以後寫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望」和「見」一字之差,意境全非。這是因為,陶淵明要表達的是自己辭官以後的喜悅,因而用「見」字,傳達出悠然自得的情懷,確有「境與意會」的效果;若改為「望」字,變成主動尋求,不僅破壞了全詩的意境,且亦不符合陶潛的節操。所以,蘇軾的體會表明他對陶詩的意境以及陶潛的為人都有比較深刻的認識。當讀者對作品中的藝術形象還停留在片斷的、分散的、表面的感性認識階段時,他們是不可能對作品的內容有全面的、深刻的感受的。只有當讀者經過深思,把那些片斷的、分散的、表面的印象集中起來,加上自己想像的補充和豐富,在自己的頭腦裡獲得形象的再現時,他才能對作品所描繪的形象有比較全面、深刻的感受,達到感受和理解的有機統一,才能透徹地領會其中的意味,得到思想感情上的陶冶和藝術鑒賞上的愉悅。
比如我們欣賞唐代邊塞詩的時候,最好就是在感受它們字面的美好的同時,也通過各種管道弄清邊塞詩詞的立意,深挖它含蓄的主旨,這樣才能從總體上對作品進行把握,欣賞到它們最深刻的美妙之處。如我們讀「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就要明白它不僅表現出了戍邊將士奮勇殺敵的英雄氣概,也讚揚了他們以身許國的豪情壯志;「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則既表達了對良將及早出現的渴望,也表現出對邊疆和平的嚮往……異彩紛呈的邊塞詩詞,或奇麗峻峭,雄渾挺拔;或清新幽雅,纏綿悱惻;或慷慨高歌,響遏雲天,或低徊淺唱,感慨萬端;或令人熱血沸騰,欲躍馬橫戈,或使人愁腸寸斷,想折戟斷刀……在面對一首邊塞詩的時候,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全面把握它:「這首詩對邊塞環境描寫有什麼特色?起了什麼作用?詩的主題又是什麼?」舉個例子,陳子昂的《送魏大從軍》(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悵別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橫代北,狐塞接雲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漢將功。)我們就可以先抓住「雁山橫代北,狐塞接雲中」這兩句,說明作者對邊塞險峻山勢的描寫裡隱含著濃郁的殺機,然後從全篇加以分析,領會其主旨,認識到它寫出了邊塞險峻的形勢以渲染氣氛,預示將來一定會有激烈的戰鬥,詩人具有異常豐富的想像能力。其主題是:寄予魏大以很大的希望,激勵友人勇立戰功;同時也表現出詩人自己為國立功的宏願。
三、文學欣賞是一種依靠想像與聯想所進行的藝術再創造活動。
藝術的想像在文學欣賞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學欣賞離不開形象,但也不是簡單的復映現象,再現形象,而是在作品形象系統的基礎上,通過欣賞者的想像、聯想,通過欣賞者的感受、理解,重新創造形象。在藝術欣賞中,讀者要為情所感,就得依靠形象所給予的具體生動的感受,以及隨之而來的想像、聯想等思維活動。特別是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由於其形象的間接性,讀者對它的欣賞,與對造型藝術、表演藝術、綜合藝術等的欣賞相比,更有待於形象的再創造,更需要形象思維的能力。它要求讀者善於通過語言的媒介,想像出作品所塑造的藝術形象和生活境界,並進而領會其思想內容。
舉個例子:沒有參加過戰鬥的讀者,能夠體驗、領略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並非由於他們頭腦裡有多少關於戰爭的概念,而是因為作家的形象描繪提供了具體可感的生動材料,它能激發讀者的想像和聯想,從而體驗和認識自己從未經歷過的戰爭生活;而親自經歷過戰爭生活的讀者,對以戰爭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往往倍感親切,有更多的體會,這是因為他們能夠以自己關於戰爭生活的經驗,來感受、想像,以至豐富、補充作品裡關於戰爭的描寫。
要是讀者不善於進行積極的想像和聯想,或缺乏必要的生活感受,那麼,再美的文學形象對他也沒有多大意義。「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唐詩中這些膾炙人口、富有表現力的詩句所勾畫的種種意境,在感受、想像能力較差的讀者眼裡,也可能是平淡無奇的。
這裡最關鍵的就是跑開想像力的駿馬或者張開想像力的翅膀。就是說,在欣賞一個作品時要根據作品中所提供的意象,在準確理解作品意旨後進行「再創造想像」,比如我們讀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詩人先描繪西湖的水光山色和晴姿雨態,再以西施為喻,寫出西湖的神韻,趣味盎然,富有美感,能給讀者以藝術美的享受。在此基礎上我們就可以通過想像領略到一種美學的原理——事物各呈面貌,各有其審美價值,可以說是善狀眼前之景,妙托物外之理。詩中所闡明的道理絕不是概念的,也不作抽象的事理演繹,而是通過西湖美景和比喻等藝術手法來表達的,是用詩的語言來說出來的,是形象的,是含蓄的,是有趣的,因此是真正的詩。
又比如,在劇本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主要通過戲劇語言來表現,然而由於劇中特有的規定場景,人物通常都不需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盤托出。他有時講得少而想得多,有時言在此而意在彼,有時說的則恰恰同想的相反,要是鑒賞劇本時,讀者不能根據劇情展開積極的思維,就不可能正確地感受和瞭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劇本內容。如《雷雨》第四幕裡,侍萍得知四鳳和周萍的關係後,悲憤地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啊,天知道誰犯了罪,誰造的這種孽!—他們都是可憐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天哪,如果要罰,也罰在我一個人身上。他們是我的乾淨孩子,他們應當好好地活著。
罪孽是我造的,苦也應當我一個人嘗。今天晚上,是我讓他們一塊兒走的。這罪過我知道,我都替他們擔待了;要是真有什麼,也就讓我一個人擔待吧。」
這是對自己的譴責嗎?罪孽真是侍萍造成的嗎?絕對不是。這是對周樸園的血淚控訴,這是對周公館為代表的封建黑暗勢力的猛烈抨擊。侍萍和他的「可憐的孩子」,都被這個萬惡的社會吞噬了——這就是《雷雨》通過藝術形象所展示給我們的真理。
由此可見,不依靠自己的想像和聯想,不經過自己積極的形象思維,讀者就不可能對作品的意境有深切的感受,不可能發現和瞭解作品中那些弦外之音、韻外之致;而讀者能夠在欣賞文學作品時,反復地品味,積極地思考,也就能從中獲得更多的感受和更深的認識。
當然,不同的讀者,由於生活經歷、文化素養、個性特點的差異,對於同一作品中的形象,也很可能得到的印象不一樣,認識不一樣。魯迅曾說過:現代的讀者看《紅樓夢》,對於林黛玉這個人物,「恐怕會想到剪頭髮,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麼模樣。」總之,和三四十年前讀者心目中的林黛玉「是截然兩樣的。」正是由於讀者在欣賞過程中對於作品形象的想像,總不免要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等而有所加工改造,於是所得的印象也就往往帶有個人特點。因此人們認為「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即欣賞者頭腦裡再現的形象,既有作品中形象的確定性與規定性,又有欣賞者的獨創性、新穎性。
四、文學欣賞是以「通感」和「共鳴」為重要特徵的一種綜合的心理感應活動。
在文學欣賞中,由於欣賞者的生活、欣賞經驗,由於各種感覺器官的暫時聯繫,視覺和聽覺之間;視覺、聽覺和觸覺、嗅覺、味覺之間往往可以相互作用而彼此溝通,從而喚起藝術形象原來不一定具有的另一種或另幾種感覺形象。這種「通感」現象是在藝術欣賞中的獨特現象。文學欣賞中的另一種心理活動——共鳴,是另外一種複雜而常見的現象。當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作家通過作品的形象表達出來的思想情操,強烈地打動了讀者,引起讀者思想感情的迴旋激蕩。他們愛作者之所愛,恨作者之所恨;為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勝利而歡樂,為反面人物的潰滅而稱快;或者為正面人物的失敗而悲痛,為反面人物的得勢而憤慨,象喜亦喜,象憂亦憂。他們為黛玉葬花而潸然淚下,為武松打虎而慷慨擊節;冉阿讓的命運,引起他們深切的關注與同情;賣火柴小女孩的遭遇,則使人們對萬惡的黑暗社會制度切齒痛恨。凡此種種,是「通感」與「共鳴」現象在文學欣賞活動中的突出特點。
比如韋莊有一首十分著名的《菩薩蠻》:
「洛陽城裡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
桃花春水淥,水上鴛鴦浴。凝恨對殘暉,憶君君不知。」
這首詞是韋莊相蜀時之作。唐亡,王建在蜀稱帝。韋莊貴為平章,卻懷思鄉之憂。遊子他鄉,思念中原也罷了,卻偏偏將思念的焦點投射到洛陽城頭。那柳枝迷離的魏王堤,那滾動著雨珠的桃花,那春水中遊蕩的鴛鴦,洛陽城裡的無限春光,在在都牽動著老詞人的思緒,想一想關山遠阻,唉,洛陽才子只能就這樣老在它鄉了……
韋莊不是洛陽人。他原籍陝西杜縣,即有名的杜陵所在地。但韋莊是在洛陽成名的。韋莊44歲時應舉入長安,遇黃巢兵至,即逃至洛陽,並在洛陽寫《秦婦吟》一篇,篇中有「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句,廣為傳誦,得「秦婦吟秀才」雅號而名知天下。這大約就是韋莊自比洛陽才子的原因吧。
而我們在讀到「洛陽才子他鄉老」這樣的文字時,如果再聯想到王灣的「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又有幾個人會不生髮出共鳴,引逗出無窮的思念之情呢?
再比如咱們洛陽人朱敦儒的《鷓鴣天·西都作》:「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疏狂。曾批給露支風敕,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
這首詞十分鮮明的袒示了作者放浪山水,傲視王侯的情懷。據《宋史》本傳載,靖康中,朝廷將作者召至京官,欲「處以學官」。作者固辭說:「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此詞當是他由汴京返回洛陽後寫下的明志之作。詞開篇即以「清都山水郎」自命,表明自已愛好山水乃是出於天性,而並非趨奉儒家「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說的矯情之舉。接著,「天教懶慢」句又進而聲稱自已的懶散的生活方式和狂放的性格特徵亦屬天賦,因而無法改變。放筆直陳中,不惟胸臆畢見,而且豪氣四溢,直摩東坡壁壘。「曾批給露」二句仍然假託天意以抒懷抱:既然天帝欽准我管理露、風、雲、月,我豈能不與之長相親和?言外頗見避世遠俗、棲心自然之意。下闕「詩萬首」三句遙接上片中的「疏狂」二字,對之進行形象化的圖解。「詩萬首、酒千觴」,既是極寫其詩思之富、酒量之豪,也見出他對詩酒鍾情之深。顯然,朗詠與酣飲於青山綠水之間,幾乎是作者的隱逸生活的全部內容。「幾曾著眼看侯王」,不僅表現了對功名富貴的鄙夷,而且軒露出卑視王侯的錚錚傲骨。較之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憤恨程度有所不及,卻更見冷峻與輕蔑。最後「玉樓金闕」二句重申不願返回朝廷、征逐名利,只願詩酒狂放、隱逸終老的心志。其中,「慵歸去」又與上片中的「懶慢」二字相應,章法雖具變化卻不失嚴密。這樣的情懷,又怎能不引發我們這些為生活的種種壓力弄得十分疲憊的人們心中強烈的共鳴呢?
綜上所述,文學欣賞是伴隨感情活動的形象思維活動,文學欣賞中的認識活動主要是一種感受體驗,而還不是評論;但是,對文學作品的形象及其所包含的意蘊,只有在正確理解作品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全面的、深刻的感受。因此,文學欣賞是感性和理性或感受、體驗和理解、鑒別的有機統一,這種統一的形式化的結果,也就是欣賞者把自己的感受準確表達出來的產品,就是文學批評。
五、寫作文學批評,是一項帶著鐐銬跳舞的審美認知活動。
文學欣賞也好,文學批評也罷,本質上說,它和文學創作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之間有著一種類似於人類血緣關係的同構效應。具體說來,它們都是通過閱讀或者寫作主體的創造性活動,使狹隘的,原本僅屬於讀者或者寫作者個人的經驗事實和情感,外化綿延成為某種跌盪起伏的激情,空寂邈遠的冥想,深邃瑰麗的語言奇觀,從而使讀者在閱讀它們的過程中獲得神奇的審美快感或精神陶冶,並因而得到自我人格的進步與完善。
雖然如此,文學批評或者說文學欣賞和創作畢竟還不是一碼事,不能等同起來。相比之下,創作是一種比較自由的精神活動。欣賞或者批評則不然,它有一定的條件和自身規定性的約束。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有限制的藝術操作活動,我把這種在限制中的文學行為稱之為「戴著鐐銬跳舞」。如果用一句更為通俗的話來說,我們還可以說它是一種「在雞蛋殼裡跳舞」的活動。
就我個人的文學欣賞和批評實踐來看,我以為要做好文學欣賞或者文學批評,大致需要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 欣賞或者評論主體要在大腦中儲存足夠大的信息量。
這些資訊,不能僅限於與你所要欣賞或者評論的物件(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等)有關的內容,而要寬泛得多。所謂「功夫在詩外」,要想準確地欣賞、評價一個作家、一部作品或一種文學現象,欣賞或者評論主體必須掌握或瞭解作家們所瞭解與掌握的一切,如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點,作家的生活與情感歷程,文學現象生成的背景、過程及影響等。不僅如此,還要瞭解某些作家本人不熟悉或不曾留心注意的東西,如他們的性格心理機制,周邊環境對他們的潛在影響等。只有掌握和瞭解了這些內容,當面對一個作家、一部作品或一種文學現象時,欣賞和評論主體才不致於手足無措,無從談起。
第二個條件,是評論主體要有足夠的敏感。
這種敏感,至少包括思想敏感和藝術敏感兩個大的方面。具體的說,就是欣賞或者評論主體要能夠在看到所要欣賞或者評論的物件後的第一時間,迅速在自己的大腦資訊庫和該物件之間做一番印證、比較和融匯工作。這時期,最重要的是抓住第一感覺,也就是我們經常談到的所謂直覺。因為直覺不僅是作家,也是評論家獲取意象的最基本的方式,只不過意象的性質有所不同而已。
直覺,簡單說來是創作和評論主體特有的一種心理能力,它一般包含三個基本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心覺。
它是指人們在接觸外界物象時的最初的心靈反應,也就是我們有時稱之為第六感覺的那種東西。心覺現象在實際情形中一般表現為人們心靈被強烈震撼或吸引的一種忘我狀態。如我們在看到一個作品的標題或一部書的封面時產生的那種像是突然間看到了一個從未接觸過的世界的感覺,或我們從燈火通明的室內出來一下子走進黑暗的原野時突然產生的那種全身心緊張,所有毛孔都豎起來了的那種現象,就屬於心覺現象。心覺是先於其它感官產生的一種知覺,它往往於不經意中左右知覺者的思維方式和思索方向。
直覺的第二個層次是感知,也就是感官對事物的直接領受或反應。
這種對客觀外物的直接經受或反應,最可貴的是使人的直覺處於一種具體、生動、新鮮、活潑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對評論物件的認識與評價往往是最準確、最切實也最富於創造性意義的。例如我們閱讀《阿Q正傳》,最重要的感知當然是阿Q及其「精神勝利法」,抓住這一點來評價作品,顯然是最易挖掘出其審美價值和認識意義的。
直覺的第三個層次是領悟,又稱頓悟。這是直覺活動的完成階段。
人們面對一種客觀物象,有了某種心靈感應與知覺後,往往會快速作出思想回饋,得出具有一定本質意義或規律性的結論,這個過程就是領悟的過程。六祖作偈,伽葉微笑,都是關於領悟的形象例證。這種領悟的結果表達出來,就是我們對客觀物象的實際認識,具體到文學評論寫作,就是對於評論物件的恰當的審美評價。
當然,直覺敏感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往往需要通過十分辛勤的努力實踐才能獲得。大量的攝取知識,潛心的分析思考,是獲取藝術敏感能力的一條最重要的途徑。
以上兩個條件是基礎,而要想真正寫出有價值的欣賞評論文字,還需具備第三個條件,即較強的傳達能力。
我們強調傳達而不是表達,因為傳達包含了輸出與接受兩個環節,是一種雙向同構的操作活動,而表達則是單向度的。所謂傳達能力,是指評論者能夠及時、準確地對對於評論物件的領悟的結果表達出來,並且能夠引起閱讀接受者興趣和啟發他們進行更廣泛深入的思考的能力。這種能力的獲得,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奏功的,同樣需要在長期持久的寫作實踐中尋求,只有在大量實踐的過程中才能培養出這種能力。
全部具備了上述幾個條件之後,就可以進入寫作過程了。表面上看,文學評論寫作似乎是張飛玩丈八蛇矛,武大郎玩夜貓子,各有各的玩法,沒有定規。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它也還是有一定條件限制的。
首先,評論者要對評論物件充分熟悉。
拿一部作品來說,你不一定要十遍八遍的讀,但細讀兩遍三遍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充分熟悉了,才可能從中發現並挖掘出對你來說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建立起你欣賞和評論的理論支點。不過,還是要特別注意一點,就是要緊緊抓住第一印象即直覺印象,否則,你的評論文字就很可能缺乏某種靈性與吸引力。
其次,得出的結論應該是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
不管是認識論的意義價值也好,審美的意義價值也好,必須是你獨自發現的,具有獨特性的,所謂有獨得之秘,否則整個文章的存在也將會失去價值和意義,最起碼可以說難以獲得較高的價值和意義。
再次,要熟練掌握和利用現有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批評方法。
這就象一個人走路,總是要先在熟悉的環境中學步,然後才能隨心所欲地去往任何地方。只有在已有的軌道上走熟了,才有可能發現它的不足甚至缺陷,也才能夠真正有所創新。
最後,還有一點是我們有志于從事文學欣賞和批評寫作的朋友要注意的,那就是:不要把文學評論寫作看得過於神妙。
文學欣賞和文學批評和我們生活中的任何事物一樣,也只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生活和行為方式而已,與其他人生行為方式並無本質的不同;也不要把文學評論看作創作的附庸,它同樣是一種獨立自足的生命存在。文學並非如獸言鳥語那樣不可理解甚至或高不可攀,以致於我們不能平視它而只能仰視它。說白了,文學是與人的心靈直接相關的東西,你要對它仰視,只會看到蒼茫的雲霧或迷亂的星空,而錯過它的真面目。只能平視它們,只有在平視時,才更容易與作家作品相互理解、溝通,也才能寫出具有真知灼見和真性情的文字。
通過以上粗淺的論述分析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文學評論寫作的確是一種有限制的操作活動,類似于「戴著鐐銬跳舞」的人類活動。不過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只要我們切實理解了它認識了它,掌握了一些必要的操作技巧,寫出較好的文學評論文章來並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希望所有願意在這些方面有所追求的朋友都能夠成功!謝謝朋友們!
李少詠(1965 — )河南西華逍遙鎮人,教授,文學博士。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洛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曾獲得河南省文學獎、河南青年作家獎、河南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發表有文藝評論、小說、詩歌、散文等三百余萬字,有評論文字《沒有人看見草生長》《傾聽與闡釋》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