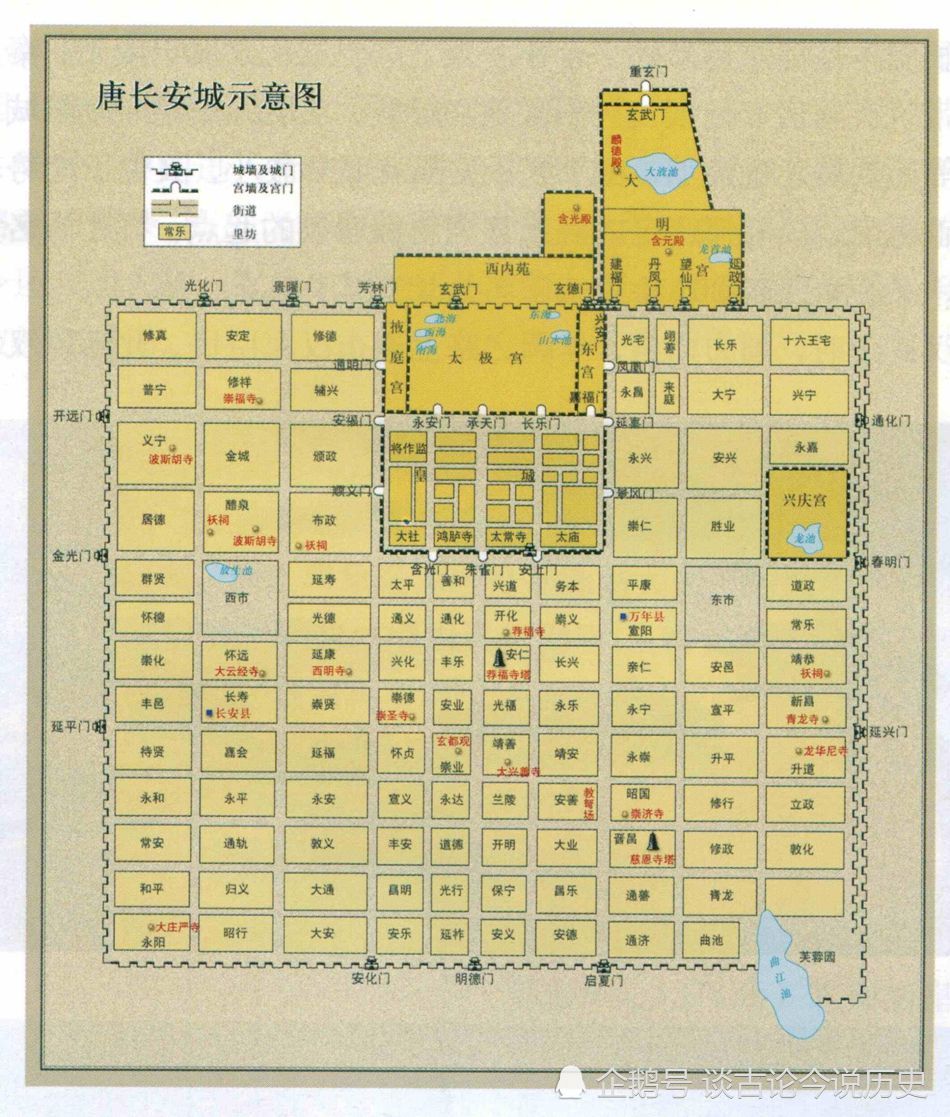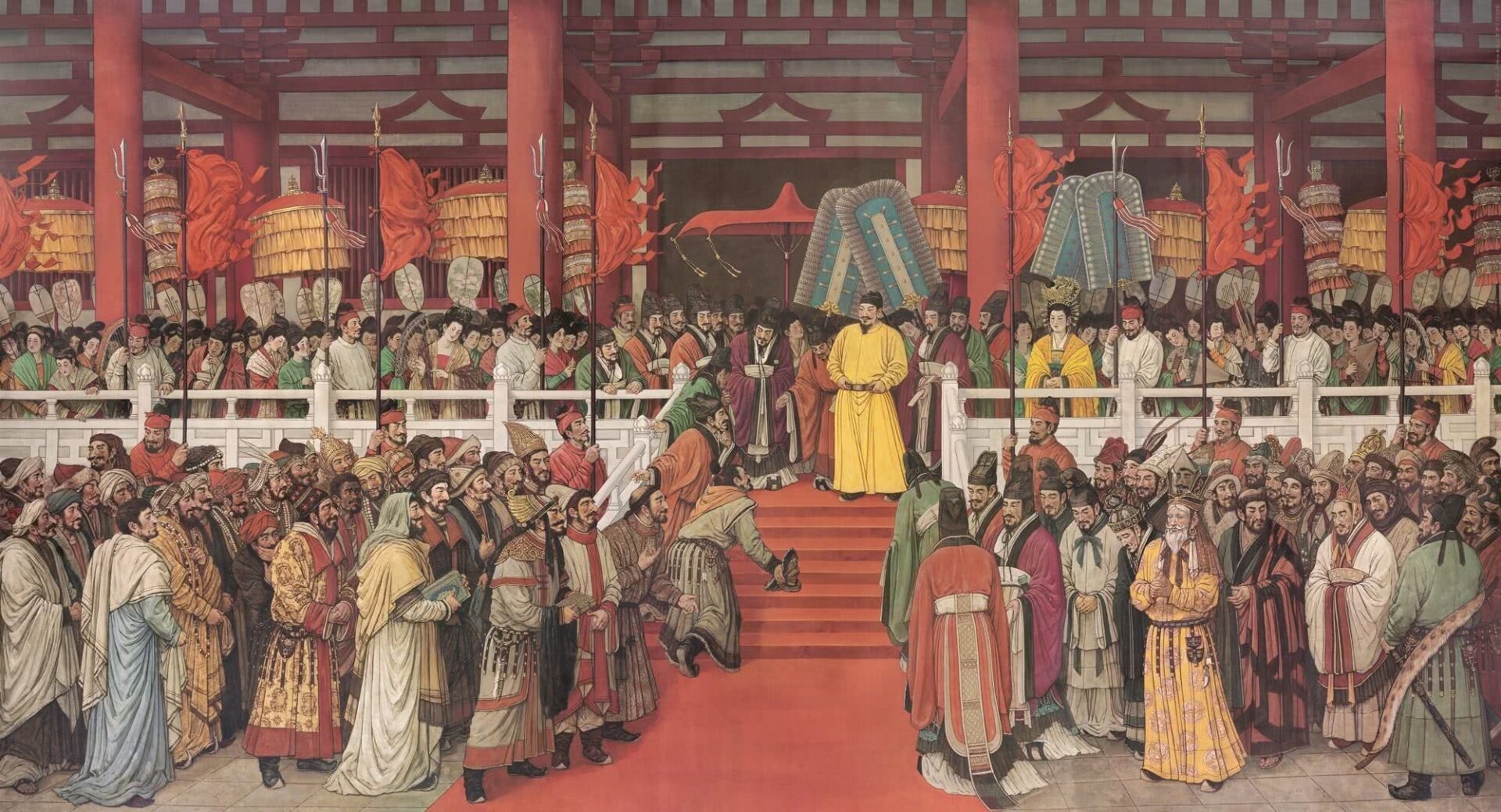大格局成就大氣韻——也說唐詩精神之美
李少詠 2021/10/12
你教孩子背的第一首唐詩是什麼?
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還是: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要我說這是唐詩最不上檯面的,跟刷在村頭村尾的「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種樹。」「戶養三頭牛,一年一層樓。」差不了太多。也就勉強押韻。
咱們漢人,傳情達意其實非常笨拙,唱不了歌,跳不了舞。
幾千年的讚歎、感懷、鬱結、愛慕、思念,甚至恍惚迷離,最美的沉澱都在詩裡頭,尤其是唐詩。
但我說的,不是你以前念的: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全唐詩》有五萬首,明星詩人那麼多,
唐詩到底應該讀哪些?
這個世界最有挑戰性的事情就是,把曾經被顛倒了的東西,再給扳回來。比如唐詩。
要我說,讀唐詩就該先讀那些最美的。
這種美,是充滿自信的盛唐氣象,
是哪管它一朝天子一朝臣,自顧自美了一千多年的大美。
以審美價值選詩,往回倒幾十年,可能要挨批判的。
於是這麼多年語文課本裡選的詩,多半就是上面你會背的那些——未必多美,但是「有意義」的詩。
但回過頭看,我們最能跟古人心有所通的,不是別的,恰恰是美。是因為人類的普遍情感而產生的共鳴。
你可能會問,美有什麼用。能當飯吃嗎?當然!
1.功利地說,美是競爭力
美是什麼?是人靠直覺感知的優化資訊。
除了邏輯、推理和計算,人還靠體驗和直覺來把握世界。
所謂審美,就是靠直覺提取優化資訊的能力。人的這種能力,恰恰是未來機器一時半會取代不了的。
在大多數人吃飽了飯的年代,更有競爭力的產品,不是最便宜的,而是更美的。
只有對美有所感悟,才能從打價格戰中脫身,在更高的領域裡奔跑。
而美,需要不斷接近和陶冶。
2.超脫點說,美能更幸福
錢掙得更多當然好,但這並不一定提升幸福感,有些人還更焦慮。
而懂得欣賞美的人,能把目標轉移到過程中,從一朵花的開放,一杯茶的滋味,一個房間的佈置裡得到愉悅。
人哪能天天加薪升職呢?懂得欣賞美,就可以隨時隨地都有幸福感,甚至創造出自己的幸福感。
繞過詩的守門人——張籍《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裡。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何)不相逢未嫁時。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你得注意,雖然我很強大,但我是最卑微的守門人——這是卡夫卡《法的門前》中法的守門人對終生徘徊於法的門前希冀得窺法的堂奧之妙,卻懾於守門人的權威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鄉下人最熱切的一次鼓勵,可惜鄉下人並未接受。鄉下人對不願放行的守門人用盡所有方法,等待、試探、乞求、賄賂——除了藐視守門人直接進入。他只看到守門人的強大,卻無視和「法」比起來守門人有多卑微。
詩有一群守門人,比如「作者生平」和「創作背景」,如果同那個鄉下一般一心取得他們的許可再進入詩,或許一生都不得進入。如若張籍的「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讓你看到了愛情中的掙扎,就別管他的真實意圖是拒絕還是招募。我們探尋真實,也珍惜錯覺,錯覺和真實一樣重要,錯覺是彼時彼地心的真實。
張籍是樂府詩的大家,和王建齊名,人稱「張王樂府」,這首《節婦吟》便是樂府舊題,是張籍最有名的一篇作品。
從字面來看,這首詩的內容是一名女子向一位愛他的男子傾吐的心聲,但一路讀下來,我們的疑惑會越來越多。
開篇便說「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這是對那位男子說:你明明知道我已經嫁了人,卻還是送我明珠以示愛。話講得很明白,隱隱有些不滿的意思,那位男子雖然很有愛情勇氣,但畢竟不合禮法。但是,對這樣不合禮法的示愛,女子並沒有嚴詞拒絕,而是「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是說我被你那纏綿的愛意所感動,便收下了這對珠子,繫在我的短衣上。
把定情的東西貼身佩戴,女子對那位男子顯然也是有意的。但作為讀者,我們就會大惑不解了:是的題目叫做《節婦吟》,主人公自然是一位貞潔烈女,卻怎麼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來呢?
詩歌寫到這裡,陡然有了一個轉折:「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裡」,女子訴說自己的婚姻家庭,「高樓連苑」意味著高貴的門第,丈夫在做皇帝的侍衛,儀表堂堂,身份不凡。可以拋棄這樣的夫君嗎?可以玷污這樣的門第嗎?我知道你對我用心良苦,那份真誠日月可鑒,但我已經立過誓,要與夫君無論生死貧富都不離不棄。那一對表達你心意的明珠,我雖然很喜歡,但終究不能接受,「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我噙著眼淚把明珠交還給你,很遺憾沒能在未嫁的時候遇到你。
就這樣,「繫在紅羅襦」的那一對明珠終於還是被女子解了下來,還給了他們原先的主人,這位女子也終於保持了一個節婦的操守,儘管戀戀不捨,儘管心有遺憾,但總算做了正確的決定。
但我們還是不能完全釋懷,畢竟在交還明珠的時候,這女子既淚水漣漣,又說出「恨不相逢未嫁時」這樣的話來,雖然身體沒有出軌,精神卻顯然已經出軌了。依照古人的標準,這樣的女子也可以被稱為節婦嗎?尤其在道學興起之後,正統思想恐怕絕難容忍這樣一個「節婦」的形象。清代沈德潛在編選那部很有影響力的唐詩選本《唐詩別裁》的時候,就是出於這個理由而擯棄了張籍的這首詩。
尤其是,張籍這首詩其實並不是在寫男女之情,而是有個副題「寄東平李司空師道」。是寫給淄青節度使、當時的一位大軍閥李師道的。那正是藩鎮割據的局面逐漸成形,唐王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日漸衰落的時候,藩鎮為了擴充實力,必須延攬人才,李師道和李師古兄弟以重金聘請頗具聲望的張籍入職自己的幕府,而這在一向以儒家正統知識份子自居的張籍看來是完全無法接受的,按照所謂正統觀念,天無二日,民無二君,中央集權大一統以外的任何政治形態都是不可想像的。
但另一方面,越是多中心的政治局面人才的價值就越高,反之亦然。所以在唐王朝仕進無門或得不到重用的知識份子們突然發現多了一些就業出口,在各大藩鎮的幕府裡也許就存在著開始自己一番嶄新的職業生涯的機遇。畢竟以數字統計看,開元以——每年來京的考生總數在一千到四千之間,而進士的名額只有30個左右,考中了也未必就有官做,還要經過禮部、吏部等等考試,所以絕大多數有志仕途的人在這條路上必將以失望收場。於是,政治原則與個人發展孰輕孰重,在這樣的時代裡就變成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投靠藩鎮的人便逐漸多了起來。
在唐代的著名詩人中,羅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羅隱才情很高,但屢試不第,路過鍾陵的時候偶遇一位舊日相識的叫做雲英的歌伎。雲英笑問他說:「十多年不見,你怎麼還沒考中?」羅隱既羞且忿,寫了一首詩來回答雲英。
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這首詩雖然談不上什麼藝術水準,卻非常有名,因為同病相憐的人實在太多了。而這位羅隱到了55歲的高齡仍然沒有在仕途上找到出路,於是去南方投奔藩鎮幕府去了,試想換做你我會不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呢?尤其是,即便是最飛揚跋扈的藩鎮,至少在名義上還是從屬於中央的。
張籍的問題還有羅隱的問題,現實中遇到是一種情況,旁觀時評價又是另一種情況。在唐代以後,漫長的中國歷史裡,中央集權大一統以外的任何政治形態始終都是不可想像的,對知識份子人格操守的要求也越來越苛刻,於是《節婦吟》的問題就是,女主角在面對那名男子的誘惑時應該採取什麼對策,這分明有著標準答案,即擲還明珠,嚴詞拒絕。只要稍有猶豫或委婉就是有損名節。
的確,我們更加欣賞的是文天祥《正氣歌》講的那樣:「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一個個都是響噹噹的錚錚鐵骨,直來直去,毫不遮掩。相形之下,張籍實在算不上個人物,雖然拒絕了李師道的邀請,但不是嚴詞拒絕,而是婉拒,寫了如此一首溫婉多情柔美動人的詩歌,一波三折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尤其是最後兩句「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雖然是明確的拒絕,但對李師道那款款的溫情至少是不會得罪這位強藩之主的。
置身事外的是好啊,臧否人物總是容易取高標準的。張籍當時,藩鎮的勢力之強,手段之厲,別說張籍這等小小的文人,就連當朝宰相也敢刺殺,朝中主張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和中丞裴度,同時遭了毒手,一死一傷,朝野上下為之震恐,李師道就是背後的主謀。試想換作你我處在張籍的位置上,面對李師道的拉攏,我們又會如何取捨呢?
誰想到一首柔美的詩歌,背後卻掙扎著如此沉重的道德勇氣和如此沉穩巧妙的心智,《唐才子傳》稱張籍「性狷直」,你這樣的性情在這等險要的關頭卻也變得知情知重了。
幕府延攬人才是中唐以後的一大社會現象,節度使們也不都像李師道那樣心懷異志,這一條用人途徑對於節度使和文士來說往往是雙贏的,名詩人李益就說過「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獻劉濟》)」,一身本領和滿腔抱負不一定要賣給帝王家,賣給藩鎮大員也不錯,而一名文士如果同時被幾家藩鎮延攬,就會贏得很好的名聲,像這位李益就受過五位節度使的延攬,韋應物在為他送行的詩裡就說「辟書五府至,名為四海聞」(《送李侍禦赴幽州幕》)。至於那些節度使,如果幕府裡面名人雲集,自己的名望也會大大提高,一旦調入中央就很可能常居相位,這就是所謂的出將入相。
天下雖然人才很多,但藩鎮也不少,所以情形就很像現在就業,雙向選擇,兩邊都很活躍。名氣很大的藩鎮延攬人才就容易很多,就像現在世界500強的大公司聘人。但一些名氣不太大的藩鎮就得多出奇招怪招才能吸引名人,所以也發生過和張籍這次《節婦吟》事件完全相反的趣事。
那是嚴宇鎮守豫章的時候,很想把名士陳陶招攬到自己的幕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甚至想出了一個美人計,派了一名叫做蓮花的美麗歌伎去邀請,但陳陶就是不應,惱的蓮花寫詩說:
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
處士不生巫峽夢,虛榮神女下陽臺。
詩中怨道美人計對陳陶不起作用,白忙一場。陳陶寫詩作答:
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心情薄似雲。
已向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一首詩表明心志,如張籍「還君明珠雙淚垂」,陳陶是「錦衾深愧卓文君」,口吻雖然有男女之別,意思卻是一般無二。
翻檢各種唐詩注本,發現很多人都把張籍對李師道的拒絕等同於對藩鎮幕府的拒絕,理由是加入藩鎮幕府就等於對抗中央。這點有必要澄清一下,藩鎮幕府並不都像李師道那樣,而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傳統,經歷過許多變化。唐代許多著名詩人都有過入幕的經歷。比如李白、杜甫、陳子昂、李商隱、杜牧等。而張籍本人患有眼疾,近乎失明,但即便這樣,韓愈還曾代他寫信來爭取入幕的機會,說明即便在張籍本人和辦主中央集權的韓愈那裡,加入幕府也未見得都是不可取的。韓愈本人也曾在科舉及第之後,因為久久通不過禮部吏部考試而被迫離開京城進了董晉的幕府,又接受了節度使張建封的經濟援助,再入張建封的幕府,其中的辛酸輾轉,韓愈在一首寫給張籍的詩裡也曾詳細講過,再強硬的理想主義者也每每會俯就現實。
善的乏力——讀張九齡《詠燕》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
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面對現實的滿目瘡痍,我欣賞張九齡「無心與物競」的超然與淡定,但我更敬重羅曼· 羅蘭「不管人生的賭博是得是損,只要該賭的肉尚剩一磅,我就會賭它」那一往無前、所向披靡的勇氣。隱士們用激流勇退、置身事外的方式來堅持操守,表達拒絕同流合污的立場,我能夠理解;但我偏激地認為,放棄鬥爭是對自己的鄙薄,對信仰的出賣,並不值得頌揚。
惡的勝利,並不是因為善的缺失,而是因為善的乏力。
《詠燕》是一首典型的詠物詩。中國詠物詩的傳統是言在物而意在物外,也就是指東打西,借物抒懷。這首詩表面是寫燕子,實際上表達了張九齡自己的政治心態。海燕分明就是自己,鷹隼分明就是政敵。
一開篇就很用心思,「海燕何微眇」,重點在「微眇」兩個字上,字面是說燕子身形很小,暗含的意思是說我只不過是個卑微的小角色;「乘春亦暫來」更有深意,所謂「乘春」,是說海燕的飛來與其說出自自己的主觀動機,不如說是得益於春光的拂照——張九齡家在嶺南,在當時是文化很落後的地方,時代稍前的禪宗六祖慧能也是這個地方的人,所以才在初見弘忍求道的時候為自己辯說「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正是武則天著意打破門閥政治,給庶族讀書人入仕做官的機會,張九齡才有可能以寒微之身官居高位,所以他可以說是武后新政的受益者,所以才有「乘春」之語,而「暫來」二字更暗示了自己不是戀棧權位的人。
接下來的兩聯,都在加深首聯的意思,重點則在尾聯「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莊子》有一段著名的故事,說惠施在魏國為相,聽說莊子也要來到魏國來,非常緊張,生怕被莊子搶走了自己的相位,於是派人手四處搜查。莊子於是找到惠施,講了一個比喻:「有一種鳳鳥,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實,非醴泉不飲。有一隻貓頭鷹抓到了一隻腐爛的老鼠,看到鳳鳥飛來,以為它要搶走自己的老鼠,便仰頭大叫,想要嚇走鳳鳥。如今你惠施也和貓頭鷹有一樣的擔心嗎?」
《莊子》的這個故事常被稱引,比如李商隱就寫過「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鴛雛竟未休」,其實這反映的正是人類一種固有的心理:總是會自覺不自覺地以己度人,尤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把這個意思寫在詩裡,李商隱的寫法就很直接,明顯對自己的敵人很不屑,而張九齡是個政治人物,話說得就很委婉,沒有把自己比作清高的鳳鳥,反而比作卑微的海燕,說泥巴裡棲身的海燕偶爾飛進華堂,只是春光造化使然,它自己絕對沒有任何的竟爭之心,鷹隼之類的大鳥實在犯不上猜忌自己。
尤袤的《全唐詩話》記述過這首詩背後的故事:那正是著名的大奸臣李林甫嶄露頭角的時期,張九齡的宰相位子越坐越不安穩。在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問題上,張九齡大大地觸怒了唐玄宗,李林甫抓住了這個機會,屢進讒言,說張九齡心懷怨謗。現代讀者恐怕不易理解,對皇帝心懷不滿,看上去無非是心裡的一點情緒而已,又不是實際犯了什麼過錯,有什麼大不了的呢?但在專制政治下,這可是極大的一條罪過,上級幾乎可以容忍下級的任何過錯,只要下級對自己足夠忠誠就好,但如果下級的忠誠度被打了問號,不管他犯沒犯錯,都應該儘早除掉。漢武帝時代的大法官張湯就是用「腹誹」的罪名除掉了政敵顏異,由頭非常簡單:顏異有一次和門客聊天,門客說起當時的一項新政存在弊端,這可是個敏感話題哦。顏大人政治覺悟高,聽完之後什麼都沒說。——的確什麼都沒說,只是嘴角微微動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使壞,這件事居然被舉報上去了。張湯秉承著一項優異的政治傳統——想整政治對手,必須一招致命——上奏說:「顏異身為朝廷高官,對政策有意見就應該直接提出來,可他倒好,嘴上不說,心裡卻暗中不滿,實在該判死罪。」
此事出於《漢書· 食貨志》,原文說:「自是後有腹非法比,而公卿大夫皆諂諛取容。」這裡的「腹非」就是我們熟悉的「腹誹」,以腹誹為由攻擊政治對手早已有之,但顏異因腹誹罪被判處死刑,這可給歷史開了先河。而李林甫此刻以同樣的罪名編排張九齡,我們已經可以想見其殺傷力到底有多大了。而在這樣的政治鬥爭裡,如果李林甫成為勝利者,朝廷上必將重演「公卿大夫皆諂諛取容」的場面。不幸的是,歷史果真重演了。
當時剛剛入秋,唐玄宗聽信了李林甫的讒言,派高力士送給張九齡一把白羽扇。皇帝有了賞賜,無論賞賜什麼,總是一種榮耀,但在這個特定的時節,送來這樣一件特定的東西,實在是大有涵義的。一個著名的典故是,漢成帝時,班婕妤受到冷落,淒涼境下以團扇自喻,寫下了一首《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裁作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扇子材質精良,如霜似雪,形如滿月,兼具皎潔與團圓的兩重意象,「出入君懷袖」自是形影不離,但秋天總要到的,等秋風一起,扇子再好也要被扔在一邊。(後來納蘭性德據此寫下了他那句著名的「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秋風畫扇,是詩詞當中的一個意象符號——扇子是夏天用的,等到秋風起了,扇子又該如何呢?)
入秋了,皇帝卻派人送來了白羽扇,張九齡淒涼地讀出了其中的涵義,作賦以獻,趕緊表明自己的心跡,又寫了這首《詠燕》送到李林甫手上。李林甫看了這首詩,知道張九齡必將退出核心政治舞臺,便不再那麼咄咄逼人了。
《全唐詩話》的這個故事,到底幾分真幾分假,我們很難判斷。但它之所以流傳,是因為它確實符合了玄宗朝張李之爭的大背景,更符合張李二人的性格。人們流傳這首詩,流傳這個故事,更因為它們傳達了一種永恆的哀歎:君子永遠爭不過小人,有底線的人永遠爭不過沒有底線的人,要臉的人永遠爭不過不要臉的人。張九齡這樣的人或許可以用《老子》的「唯其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來安慰自己,而事實上,正是他們的「不爭」,正是他們高姿態的「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才使他們永遠吃虧受屈,永遠在人事鬥爭中倉惶敗北。這或許是一個永恆的悲劇。
看不見的城市——讀李賀《天上謠》
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雲學水聲。
玉宮桂樹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纓。
秦妃捲簾北窗曉,窗前植桐青鳳小。
王子吹笙鵝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
粉霞紅綬藕絲裙,青洲步拾蘭苕春。
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生石山下。
李賀(約790年——約816年)字長吉,河南府福昌(今河南宜陽人),這裡道教風氣很盛,附近有道教名山女幾山,前文提到過的仙女杜蘭香傳說就是在這裡升天的。李賀是李唐宗室高祖叔鄭王李亮之後,頗愛炫耀這個血統,他一生經歷了德宗、順宗、憲宗三朝,那正是藩鎮、宦官亂政的時期。
雖然是李唐宗室之後,但李賀家道早衰,更因父親的名字裡有個「晉」字,與進士之「進」諧音,要避「家諱」便沒法參加科舉考試,才華橫溢的李賀終於受到皇帝的眷顧,在首都長安做了3年了奉禮郎,這是個九品芝麻官,管理一些婚喪禮儀的事情,李賀從小體弱多病,短短的一生常在吃藥,去世時年僅27歲。
李賀被稱為「鬼才」,他的詩歌風格在整個唐詩世界可謂獨樹一幟,一眼就可以辨認出來。李賀和李商隱都有唯美主義傾向,但是李賀成為李賀的是它獨有的超現實主義傾向,就像達利的畫,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越假越美麗。
在作詩的方法上,李賀也和別人不同,大多數人最欣賞的作詩方法是像李白那樣的,鬥酒詩百篇,情緒一上來就可以倚馬千言,文不加點,我們習慣上稱之為感情的自然流露;相反,大多數人最不能接受的作詩方法是像孟郊、賈島那樣的,為了一個字就可以推敲好幾年,是為「苦吟」,我們會認為這是「為創作而創作」,是錯誤的。
但李商隱和李賀都屬於「苦吟」的一類。吳炯《五總志》說,李商隱下筆寫作之前,要做大量的資料搜集工作,把書堆的到處都是,所以,時人稱之為獺祭魚——據說水獺捕到了魚不是馬上吃掉,而是先把魚兒整整齊齊地排列在岸邊的石頭上,很像人類在搞祭祀禮儀。
材料掌握得越多,使用起來也就越狠,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詩句:「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喜雪》)一連四句詩句句都在用典,對於缺乏同等閱讀體驗的讀者來說句句都是攔路虎。
李賀比李商隱吟得更苦,雖然他7歲的時候就可以快刀斬亂麻裡寫成長文,讓韓愈這樣的文章大家歎為觀止,但長大以後完全變了樣,每天一早騎著一匹弱馬出門,背著一個錦囊如果想出了什麼詩句就趕緊記下來,投到錦囊裡,記下的都是零星想到的短句,並沒有事先定下一個題目,圍繞著這個題目構思,等天黑了,回來——從錦囊裡把那些零星的詩句都拿出來,或棄或取,排列組合——完整的詩篇就這麼成型了。李賀的母親常常打開那個錦囊,如果看到詩句太多,就會又生氣又心疼地說:「這孩子是白要把心嘔出來呀!」(《新唐書.藝文志》)
如果這個故事確實是真的,那就意味著李賀其實很像電腦程式的作詩機,在寫作之初並沒有一個確切的要表達的東西,是有毫無目的的散句來做排列組合。如果說這是意識流的手法,卻完全沒有「流」的過程,巧合的是,英國唯美主義領軍人物人物王爾德也是這麼作詩的,所以得到過「支離破碎」的批評,而從「苦吟」的標準來看,李賀絕對要比孟郊、賈島更進一步了,所以張振鏞有過這樣一個評價:孟郊和賈島雖然是郊寒島瘦,但不失奇崛之氣。李賀和盧彤則由奇崛走入了幽冷怪僻。
作者簡述
李少詠(1965 —— )河南西華逍遙鎮人,教授,文學博士,先後任教於周口師院、洛陽師院。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洛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曾獲得河南省文學獎、河南青年作家獎、河南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發表有文藝評論、小說、詩歌、散文等三百餘萬字,有評論文字《沒有人看見草生長》《傾聽與闡釋》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