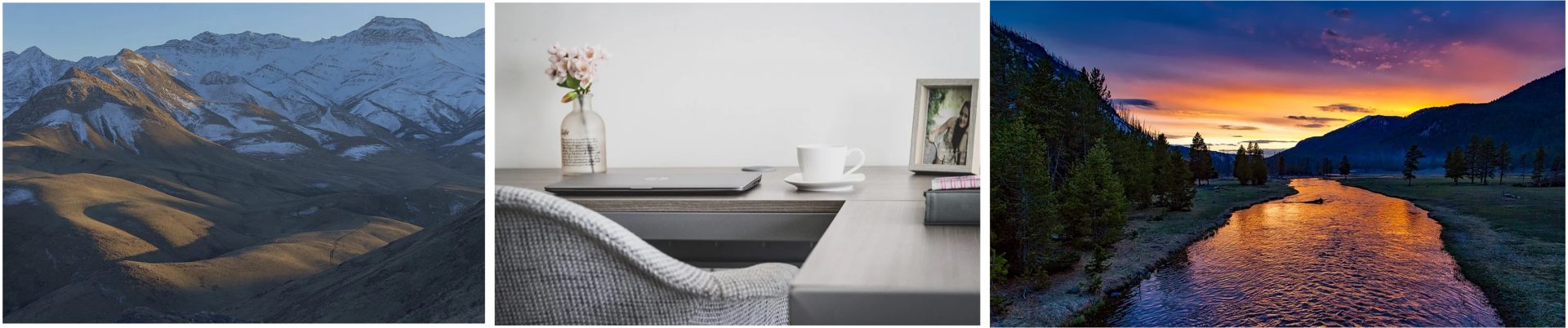近觀溫力憲大寫意人物畫創作
李少詠(小木匠)2021/11/22刊
在一個雨後的黃昏,一片清新明淨空曠寂寥的綠草地上,偉大的塞尚以一種剛從遙遠神秘的天國漫遊了一遭歸來的熱病患者囈語般的聲音,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的畫家是人類的里程碑——從洞穴壁上好的馴鹿到馬奈的峭壁——從棲居埃及墓穴裡的獵手、漁夫,從龐貝的滑稽場面,出比薩和錫耶納的壁畫,出委羅內塞和魯本斯的神話創作,出所有這些作品中傳給我們的,是同一種精神……我們都是同一種人。在這條彩色的鏈條上,我將加上又一個換——我自己的藍色的環。
一個世紀以後,一位名叫溫力憲的年輕中國人,也在這條彩色鏈條發出的炫目光輝中,以一種捨我其誰的孤獨英雄的蹣跚步態,醉酒般向我們搖擺而來。
溫力憲有一頭鋪天蓋地濃如墨亮如漆柔軟如錦緞的黑髮,這頭黑髮如一道神秘的風景,與常掛在嘴角的那一抹自嘲也許是自慰的苦笑一起,共同構成了一張連接著藝術家靈魂的青銅面具。這張青銅面具的靈性與張力集中在上面那一雙朦朧迷離的小眼睛中悄悄地漫溢出來,充塞了整個世界。那雙朦朧迷離的小眼睛冷、癡,像水,像霧,更像一頭正在覓食的美洲黑豹,刹那間便能迷醉你渴尋美好千百年而不得的心靈。
就是這雙朦朧迷離的小眼睛帶著他,遠走天涯,走進了中國藝術精神的深處,走出了一方中國大寫意人物畫的新天地。
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大寫意的民族,龍的形象的創造及有關的無數神話傳說就是最典型的例證。然而長久以來。中國美術發展史卻讓花鳥佔據了大寫意精神的最高殿堂。王維、梁楷、鄭思肖、石濤、八大、徐青藤,以至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無不是以大寫意花鳥而贏得大師稱號的。而作為萬物之靈長的人物則歷來被認為再現性強表現性弱,寫意有過多的束縛,因而難成大氣候,所以少人願意或者說敢於問津。
在坎坷與挫折中度過了自己青少年時代的溫力憲偏偏不信這個邪。考察了中外美術創作史之後他獨具慧眼地認識到,中國大寫意人物畫是一種最宜於超然物外而又富於靈性與才華的藝術家靈魂棲息的最佳境界。於是,他開始; 十年磨一劍的不懈探索與追求,終於在一片喧嘩與騷動的當代美術界創造出了一方完全屬於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世界其實很小很小,心的領域很大很大。對於溫力憲來說,創作就是一切。儘管,浮現在他那副靈魂的面具上的常常是一絲輕鬆散漫的苦笑或者是一抹似有若無的淒清,但他的內心深處,卻是一個內涵無限豐富的美麗的宇宙。他那幅《笠翁垂釣圖》,仿佛只是上蒼餘無意間借他的手胡亂的、隨意地塗抹了幾筆,卻畫出了一種無限博大無限深刻的清靜與蒼茫。那位頭戴蓑笠沿江垂釣的老漁翁蹲在那裡已經有多久了?沒有人知道。也許,已經有了一萬年了吧?你看那釣線,那似有若無的釣線已經被時間的煙霧薰染成了一副如歷史本身一般蒼茫朦朧的灰紅顏色,他的身影,也已經成為了一座同樣如歷史本身一般堅實沉厚的山石或者說巉岩。也許,他蹲在那裡只不過才一瞬間。君不見那朵恬然淡然悠然怡然的微笑,還悄悄地掛在他滄桑歷盡的唇邊沒有消失,而那只精緻如一幅宋人寫意小品一般的小小的魚簍,也才像一個迷迷濛濛中從甜夢中醒來的孩子剛剛張開了朦朧迷離的睡眼呵!所謂“一死生,齊萬物”,看他這份恬然淡定萬物不縈於心的怡然超然安然的形神意態,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也許他就是已經能夠通過內省時空,彌合了現實人生與個體內心世界的所有可能的矛盾與裂痕的晚年的東坡先生蘇子瞻吧。也許,也許更切近一步,那位也許很老,也許還很年輕的蓑笠垂釣者就正是已經本質物件化了的畫家溫力憲本人,誰又能完全說得清楚呢?我們欣賞一件藝術作品,正如隨便拿一把意念的鑰匙去開一把存在之鎖,不論開開開不開都要隨心隨緣就如閑看花開花落坐望雲卷雲舒一樣,對不對?
一個藝術家的誕生與生成,往往是伴隨著某種持續不斷的自我犧牲甚至人格的損傷以至於隳毀的過程,藝術家的誕生與生成過程中的以物質自我為中心的人的犧牲與隳毀,這是中外藝術史上一個不爭的事實。表面看來,這一點很可怕,而事實上,它卻是一種精神意義上的再生的先兆。舊的自我人格的犧牲或者說毀滅,正意味著某種新的,更富於創造性好生命活力的新人格的開始形成。溫力憲的作品透示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不斷揚棄又不斷創造的、充滿野性的癲狂與不可思議的衝擊力的文化精神。
作品的風格也就是藝術家的風格。溫力憲把文化典籍好民間傳說中仙風道骨紫氣縈繞的道家始祖老子畫成一位騎在一頭古裡古怪的老牛的背上牧歸的童心老人,在更高層次上顯示出了一種根植於華夏大地的中國人靈魂與人性的潔淨和純美。隱藏在畫家那副靈魂的青銅面具背後的那一份無與倫比的仁慈與喜悅、寧靜與超然,在一種如詩如畫如歌如夢的水墨精神中隨著那淳樸稚拙的一人一牛於暮色蒼茫的溶金落日裡緩緩向我們走來,在我們眼前幻化為無數美麗絕倫的彩蝶一般飄舞飛翔的綺麗夢幻。這時候,一種看不見的力量,也許是上帝那只神奇的具有極大法力的大手中衍射出來的力量,也許就是畫家本人那經過了千辛萬苦曲折艱難的死亡與再生的複雜過程之後形成的新的人格力量的作用下,逐漸凝聚成為一個無比絢爛無比誘人的七彩光環,就像我們的夢中那位手執橄欖枝的女神一樣,引導著我們朝著某種理想的境界飛升而去。
在意境營造方面,溫力憲可以說是一位具有非常出色的天才稟賦的畫家。他善於通過一些最簡單最質樸的線條或者色彩,甚或僅僅只是通過一些充滿智慧的靈性閃光的空白,把自己如深蘊於千萬米之下的地殼深處的岩漿一般的激情和人格魅力不動聲色地展示出來,讓我們這些觀賞者、閱讀者、批評者隨著他靈魂律動的節拍而激動、哀傷或者,瘋狂。僅僅看一些他的水墨作品的名字、題款,你就能夠於無所有的意識的空間中看到一個個旋舞律動著的人類精神或者靈魂的也許十分恬淡優雅也許極度亢奮張揚的藝術造型。《雙翁共釣一荷塘》,《花心愁欲斷》,《小舟天涯遠》,《僧廬聽雨圖》……人類與生俱來的生命的大歡樂、大悲苦、大寧靜、大自在,盡在不言中了。
最讓人心動心儀感慨不已的是溫力憲筆下形態各異的羅漢形象。第一次撼動我還算比較堅硬的心靈的是溫力憲的《八羅漢圖》。在雙目接觸它的第一個瞬間我就隱隱約約地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幅水墨與宣紙簡單融合而成的所謂繪畫作品,它更是一幅關於人類生命存在的形象外化,是一段人的生命歷程尤其是精神歷程的形象化的歷史演繹。畫面上的八位元羅漢表情、神態雖然各個不同,卻都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操縱與控制下,呈現出某種神奇的放射性狀態,由四面八方彙聚於一點。那一點的所在,也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也許是嬰兒在經歷了千辛萬苦的跋涉和搏殺之後終於佔據了母親靈魂和肉體統一了的制高點因而愉快放鬆地脫離母體衝殺出來的那最初的一刹那。正如已經飄然遠逝了的女作家陸星兒曾經在某一個繁星當空的夜晚面對浩渺無垠的天空和蒼茫無極的大地時所發出的那一聲餘音至今不絕的浩蕩感歎:“那一瞬間如此輝煌!”
的確,在我們的視線籠罩下,畫面中的一切都在旋轉,一切都在變化,一切都在發生、發光、發熱,發出足以燃燒起許多人內心的欲望和激情的神秘力量。生命的歡歌奏響了,塵世的鐘聲敲響了,野性的靈魂復歸了,生命的冰河解凍了。在足以這籠罩一切融化一切激發起一切人類原始欲望的生命大合唱中,一個孤獨的靈魂擊水為拍踏土作歌,飄飄搖搖,從茫無邊際的生命荒原上向我們走了過來。
也許是積聚了太多太多因了塵世的嘈雜與喧囂引發的直接作用於人的精神與靈魂的無邊的沉鬱和傷感,也許是那久蘊於心的一旦爆發便足以沖決一切世俗樊籬和精神羈絆的理想與渴望在惡濁的現實空氣中受到了太多太多有心或者無意的扭曲與壓抑,隱藏在溫力憲那副青銅面具後面的那顆藝術家的靈魂總是顯得過於沉重過於傷感過於迷茫過於孤寂以至於總是給我們這些閱讀者和欣賞者帶來某種無法言喻的淒苦迷離之感。他的作品,自然也就總是帶著一股無法排遣的、天涯孤旅一般的孤寂落寞淒清哀怨。不獨他筆下的閨中曠婦孤僧羅漢如此,臥薪嚐膽滿腹苦水的越王勾踐身受腐刑發憤著書留下“千古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太史公司馬遷如此,對花傷情望月流淚的漂泊士子落拓文人如此,就連《牡丹仕女圖》中那位在牡丹仙子托舉下飄然欲飛的青春少女,那雙美麗絕倫的眼睛中所流露出來的,也一樣是一絲絲淡淡的幽怨淡淡的哀傷淡淡的無法言喻的淒苦與無助。
當生活過於苛刻,苛刻得只留給你一抹無以言狀的苦笑,連風花雪月也被悄然地、無聲無息地關進由他人或者就是你自己心造的牢獄的時候,你,一個還有一份精神沒有被世俗完全消弭了的知識份子或者更直接一點說一個以精神產品創造為志業的藝術家、藝術創作者,你該怎麼辦?我想,毫無疑問的,你會像你自己,像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本來就應該的那樣,隨手端起身邊的酒杯、茶杯也許是咖啡杯,將裡面的醇酒、殘茶或者咖啡一飲而盡,讓那烈酒、那濃茶或者那滾燙而且帶有強烈的苦澀意味的咖啡來刺激一下你在世俗的重重包圍中已經逐漸變得有一點點麻木或者說遲鈍了的感覺。有人說,亂世喝酒,盛世飲茶。而我則以為,無論何時何世,沒有沉醉過的人生,不是真正的人生;沒有瘋癲過的愛情,不是真正的愛情;而沒有如高更、梵古、徐青藤那樣迷失過、癡狂過的藝術家,則絕對不能算是真正的藝術家。對於你,我想,這樣的說法應該不會不合適而引發反對的,是不是?
溫力憲很窮,窮到了只有苦笑的地步。他不會喝酒。嚴格意義上也不會飲茶,甚至喝起咖啡也只會把眉頭皺成兩座不太規則當然也不太好看的山峰,嘴裡連連叫著“苦呵苦呵”。可是,那又有什麼?不會喝酒,他會拋卻此生拼一醉。有了那一拼一醉,也就有了大境界,大寧靜,大輕鬆。從而也就有了筆下那位醉臥山崗的大肚羅漢。某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擺脫孤獨與壓抑的渴望在酒力的作用下從山岩一般堅硬厚重的青銅面具後面鑽出來,投注在這尊有著和畫家本人一樣的一抹苦笑的羅漢的身上,立即顯示出一種令人心弦震顫,欲哭無聲的巨大力量,讓你不由自主地,也是別無選擇地想要拋卻世俗的一切羈絆與約束,和他一起癡狂一起發癲一起,醉臥山崗。然後,一起等待酒醒,攜手挽臂,伴他走完後面那一程說不上時間長短也說不上是痛苦還是歡樂的,天涯之旅。
傳說中,當年一代畫聖吳道子曾經應邀畫成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可以想見,那是怎麼樣一種奔放灑脫,怎麼樣一種汪洋恣肆的氣度和境界。而作為一位生活、工作和創作在二十世紀以來的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藝術家,溫力憲也同樣通過艱苦卓絕的自我修煉與努力達到了那種“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的恢宏高超的審美境界。他的長達二十餘米的人物長卷“行人一走天涯”,既有唐賢的恢宏氣度,又有宋哲的高妙法理。結構嚴謹而筆墨多變,既有咫尺千里之勢,又有曠達疏放之概。雖然還沒完全避免那種隱隱約約憂鬱哀傷孤寂寥落之感,卻已經透示出了一個優秀藝術家走向大師之路的某些基本特質,也為將來的美術史冊上屬於他的那一個鏈環添上了迄今為止最有力度的一筆。
“行人一走天涯”,也許這正是溫力憲靈魂的青銅面具背後的真實內心世界的最為鮮明的揭示了。而且,也許只有在這種永遠孤寂落寞哀傷幽怨的天涯之旅中,溫力憲的藝術創作之樹才能始終保持某種靈性與活力,從而實現長青不敗的終極目標。
作者李少詠
李少詠(1965 —— )河南西華逍遙鎮人,教授,文學博士,先後任教於周口師院、洛陽師院。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洛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曾獲得河南省文學獎、河南青年作家獎、河南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發表有文藝評論、小說、詩歌、散文等三百餘萬字,有評論文字《沒有人看見草生長》《傾聽與闡釋》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