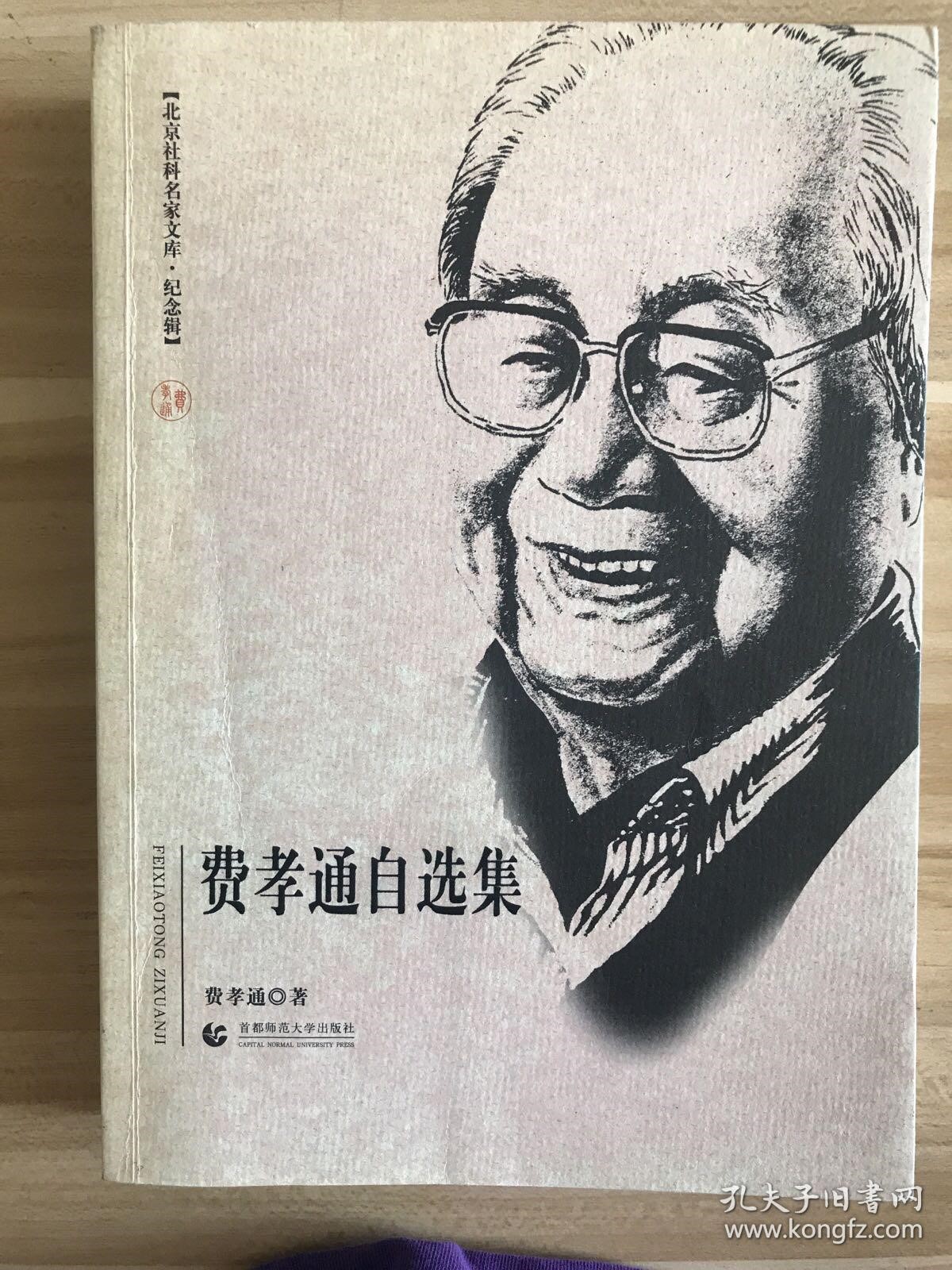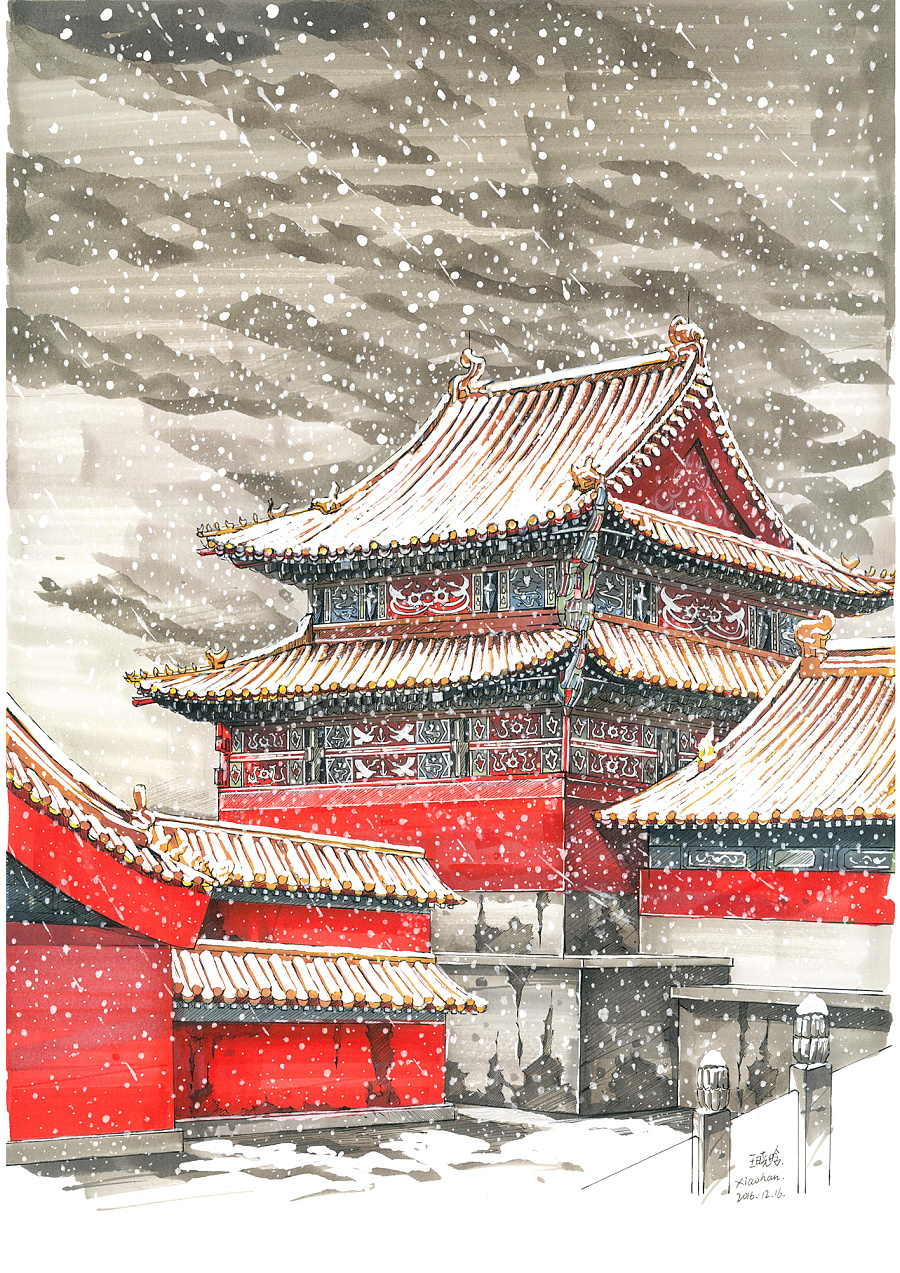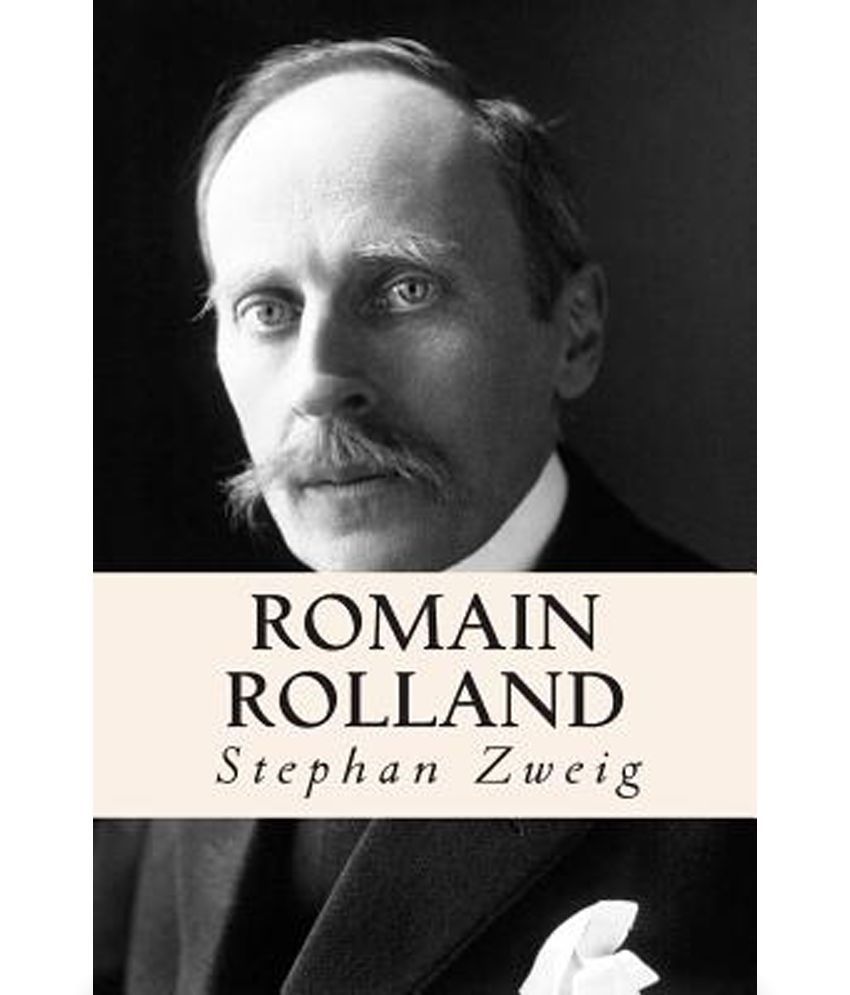費孝通與潘光旦的差距,就是我們與費孝通的差距
李常生整理 2022/04/25 原刊於群學書院
紀念費孝通先生逝世17周年
這大概是中國社會學史上最令人難過的一幕了:
1967年6月10日,因為得不到必要的醫治,身染沉屙的潘光旦教授即將走到生命的終點。這時,他的身邊沒有一位親人,老保姆只能叫來住在隔壁的費孝通教授。面對這位彌留之際的老師、同事、好友,費孝通一籌莫展,他連一片止痛片也拿不出來,唯一能做的,是把他抱在懷裡。幾個小時後,潘光旦在費孝通的懷中停止了呼吸。
又過了三十二年,潘光旦墓木已拱,費孝通也已年近九旬,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社會學家。當他接到參加潘光旦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的邀請後,一夜無眠。在紀念活動上,發表了這篇著名的講話。費孝通先生講道:
我覺得,關鍵是要看到兩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間,中國知識份子兩代人之間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兒呢?我想說,最關鍵的差距是在怎麼做人。做法不同,看法不同。
他們首先是從己做起,要對得起自己。怎麼才算對得起呢?不是去爭一個好的名譽,不是去追求一個好看的面子。這是不難做到的。可是要真正對得起自己,不是對付別人,這一點很難做到。考慮一個事情,首先想的是怎麼對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給別人看,這可以說是從“己”裡邊推出來的一種做人的境界。
做一個什麼樣的人,自己才能覺得過得去?不是人家說你過得去,而是自己覺得過得去。這一點,在兩代知識份子之間差別很大。潘先生這一代和我這一代就差得很遠。我同上一代人的差距有多大,我正在想。下一代人同我的差距有多大,也可以對照一下。通過比較,就可以明白上一代人裡邊為什麼有那麼多大家公認的好人。
如今,費孝通先生去世也已經十七年了。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早已日新月異,但在費孝通先生心心念念的“做人”這一點上,我們要向前輩學習的太多太多。
潘光旦(1899-1967),哥倫比亞大學理學碩士,先後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中央民學院等校任教,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民族學家。曾有人把他與梅貽琦、葉企孫、陳寅恪並稱為“清華四大哲人”。
費孝通(1910-2005),倫敦經濟學院博士,先後在雲南大學、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校任教,享譽世界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
本文系費孝通先生在1999年紀念潘光旦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張冠生根據錄音整理。文稿原載於《讀書》1999年第12期。
一、
接到參加紀念潘光旦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的通知,我就開始想該怎麼講,花了很多時間。晚上睡覺的時候也在想這個問題。在這個會上,怎麼表達我的心情呢?想了很多,也確實有很多話可以講講。
可是我來開會之前,我的女兒對我說:不要講得太激動,不要講得太多。我馬上就到九十歲了,到了這個年齡的人不宜太激動。可是今天這個場合,要不激動很不容易。
我同潘先生的關係,很多人都知道。我同他接觸之多,關係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兒之外就輪到我了。從時間上看,我同潘先生的接觸要比他有的女兒還要長一些。小三出生之前,我已經和潘先生有接觸了。我們是在上海認識的,時間是一九三〇年之前,早於我來北京上學的時間。後來,在清華大學,我和潘先生住得很近,是鄰舍。到了民族學院,住得更近了。有一個時期,我們幾乎是天天見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說是生死與共,榮辱與共,聯在一起,分不開了。這一段歷史很長,我要是放開講,可以講上半天。
二、
昨天晚上我還在想,要講潘先生,關鍵問題在哪裡?我覺得,關鍵是要看到兩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間,中國知識份子兩代人之間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兒呢?我想說,最關鍵的差距是在怎麼做人。做法不同,看法不同。做一個什麼樣的人,自己才能覺得過得去?不是人家說你過得去,而是自己覺得過得去。這一點,在兩代知識份子之間差別很大。潘先生這一代和我這一代就差得很遠。他是個好老師,我不是個好學生,沒有學到他的很多東西。
潘先生這一代人的一個特點,是懂得孔子講的一個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麼叫做“己”,這個特點很厲害。己這個字,要講清楚很難,但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礎。歸根到底,要懂得這個字。在社會上,人同別人之間的關係裡邊,有一個“己”字。怎麼對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個“吾”,是“己”。在英文裡講,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弄清楚這個“self”是怎麼樣,該怎麼樣,是個最基本的問題。可是現在的人大概想不到這個問題了。很多人倒是天天都在那裡為自己想辦法,為自己做事情,但是他並不認識自己,不知道應當把自己放在什麼地方。
潘先生這一代知識份子,對這個問題很清楚。他們對於怎麼做人才對得起自己很清楚,對於推己及人立身處世也很清楚。不是潘先生一個人,而是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這樣。他們首先是從己做起,要對得起自己。
怎麼才算對得起呢?不是去爭一個好的名譽,不是去追求一個好看的面子。這是不難做到的。可是要真正對得起自己,不是對付別人,這一點很難做到。考慮一個事情,首先想的是怎麼對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給別人看,這可以說是從“己”裡邊推出來的一種做人的境界。
這樣的境界,我認為是好的。怎麼個好法,很難說清楚。如果潘先生還在世的話,我又該去問他了。在我和潘先生交往的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我把他當成活字典。我碰到不懂的問題,不去查字典,而是去問他。假定他今天還在,我會問,這個“己”字典出在哪兒?在儒家學說裡邊,這個世界的關鍵在什麼地方?為什麼它提出“推己及人”?“一日三省吾身”是要想什麼?人在社會上怎樣塑造自己才對得起自己?
潘先生在清華大學開過課,專門講儒家的思想。我那時候在研究院,不去上課,沒有去聽。後來我想找到他講課的時候別人記錄下來的筆記。新加坡一個朋友叫鄭安侖,聽過潘先生的課。我要來了鄭安侖的課堂筆記,可是他記得不清楚。我後來想,其實不用去看潘先生講了些什麼,他在一生中就是那麼去做的。他一生的做人做事,就是儒家思想的一個典型表現。他不光是講,更重要的是在做。他把儒家思想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現了出來,體現了儒家主張的道理。
三、
這個道理關鍵在哪裡?我最近的一個想法,是覺得關鍵在於“己”字。“己”是最關鍵、最根本的東西,是個核心。決定一個人怎麼對待人家的關鍵,是他怎麼對待自己。
我從這個想法裡想到了自己。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講我看人家怎麼看我。潘先生同我的一個不同,是他自己能清楚地看待自己。我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裡做個好人,在做人的問題上要個面子。現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這個面子已經是個問題了。我這一代人還是要這個面子,所以很在意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一點很難做到。這個問題很深,我的力量不夠,講不清楚,只是還可以體會得到。我這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有這個問題存在。
孔子的社會思想的關鍵,我認為是推己及人。自己覺得對的才去做,自己感覺到不對的、不舒服的,就不要那樣去對待人家。這是很基本的一點。可是在現在的社會上,還不能說大家都是在這麼做了。潘先生一直是在這麼做的。這使我能夠看到自己的差距。我看人看我,我做到了,也寫了文章。可是我沒有提出另一個題目:我看我怎麼看。
我還沒有深入到這個“己”字,可潘先生已經做出來了。不管上下左右,朋友也好、保姆也好,都說他好,是個好人。為什麼呢?因為他知道怎麼對人,知道推己及人。他真正做到了推己及人。一事當前,先想想,這樣對人好不好呢?那就先假定放在自己身上,體會一下心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我今天講潘先生,主要先講這一點。我想這一點會得到大家的贊同,因此可以推廣出去,促使更多的人這麼去想、這麼去做。現在的社會上缺乏的就是這樣一種做人的風氣。年輕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應當怎麼去做。
四、
要想找到自己,辦法是要知道自己。不能知己,就無從“推己”。不能推己,如何“及人”?儒家不光講“推己及人”,而且講“一以貫之”,潘先生是做到了的。我想,潘先生這一代知識份子在這個方面達到的境界,提出的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
現在,怎麼做人的問題,學校裡不講,家裡也不講。我們今天紀念潘先生因此很有意義。怎麼做人,他實際做了出來。我作為學生,受潘先生的影響很深。我的政治生命、學術生命,可以說和潘先生是分不開的。我是跟著他走的。可是,我沒有跟到關鍵上。直到現在,我才更清楚地體會到我和他的差距。在思考這個差距的過程中,我抓住了一個做人的問題,作為差距的關鍵。我同上一代人的差距有多大,我正在想。下一代人同我的差距有多大,也可以對照一下。通過比較,就可以明白上一代人裡邊為什麼有那麼多大家公認的好人。
潘先生這一代人不為名、不為利,覺得一心為社會做事情才對得起自己。他們有名氣,是人家給他們的,不是自己爭取的。他們寫文章也不是為了面子,不是做給人家看的,而是要解決實際問題。這是他們自己的“己”之所需。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受些啟發,多用點腦筋,多懂得一點“己”字,也許就可以多懂得一點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有一種超越自己的力量。有些文章說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實上他沒有覺得冤。這一點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這是歷史的必然。他沒有怪毛澤東。他覺得搞到那個地步不是毛澤東的意思。為什麼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澤東會是什麼樣的做法,那根本不會是這個做法。因此不應該怪他。這就是從“己”字上出來的超越一己榮辱的境界。這使潘先生對毛澤東一直是尊重的,是尊重到底的。他沒有覺得自己冤,而是覺得毛澤東有很多苦衷沒法子講出來,也控制不住,最後演變成一場大的災難。
潘先生經歷了災難,可是他不認為應該埋怨哪一個人,這是一段歷史的過程。潘先生是死在我懷裡的,他確實沒有抱怨,沒有感到冤,這一點我體會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們很難學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認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