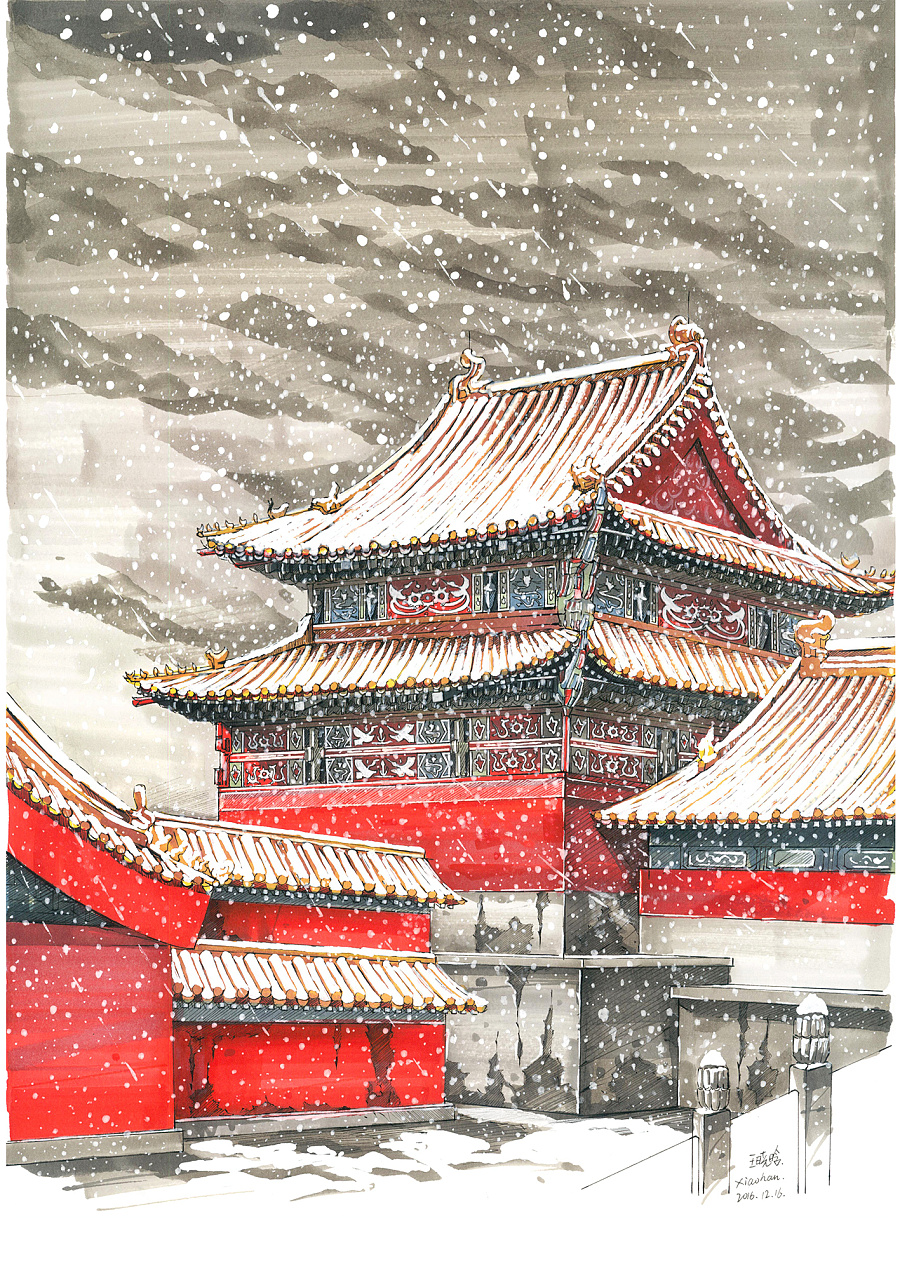我文學路上的掌燈人
閆紅 2021/12/06 刊
我五歲那年,搬到父親所在報社的家屬院。我家在巷子裡靠西邊,東邊的院子空著,高高地長滿了草,夏天裡會開出花朵,有風沒風都輕輕曳動。我經常一個人溜進去,唱歌,跳自己編的舞蹈,像個原始人,體會那沒有章法的快樂。
空院子朝東是某官員家,官員尚且客氣,官員夫人卻很倨傲。有幾次我媽下夜班,推車經過她家門口,車輪碾著本來裝得就不很穩當的水泥板路,咣當聲驚動了她。她衝出來大罵,用詞十分強悍惡毒,我媽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懂官民差距,兩人大吵一架,就此交惡。
再朝東就臨近巷口了,住著王叔一家,他們家異常地安靜,只是偶爾會飄出琴聲,是他們家女兒在練琴。王叔是副刊編輯,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大學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算得上高學歷。有幾回,我在我爸辦公室裡寫作業,王叔閑閑地踅進來,丟過來一本《詩歌報月刊》或是別的什麼,上面往往是他的新作,讓我心氣極高的老爸,也為之嘆服。
王叔的妻子與他氣質相似,身材高挑,面龐雍容又清秀,我爸老說她像個朝鮮族人,大概指她身上那種沒有煙火味道的清爽吧。
在當時普遍雞飛狗跳的生活中,王叔一家活出了某種優裕的規整,我本能地有一種距離感,遠遠看見了心裡也會犯難,不知道該不該像對別的叔叔伯伯那樣打一聲招呼。我隱隱感到,他看不上這些俗世規矩,況且,許多時候,他的眼神也是飄忽的,我就是打招呼,他也看不見吧。
這種狀況到我十四歲那年被打破。那年我讀初二,學習成績一般,唯有作文寫得還行,青年節前,班主任囑我寫首詩在學校的慶祝活動上朗誦,我花了一節數學課的時間,寫了出來。
在家裡試著朗誦時,被我爸聽到了,他當然認為這是一首佳作,但殘存的理性告訴他,還是應該聽一聽業內人士的意見。他拿著這首詩,來到王叔家,王叔看完後,說:“不錯,不錯”。
這讓我爸更加興奮,說王秋生向來眼高於頂,能說兩個“不錯”,那一定是真不錯。又過了幾天,我爸說,王叔讓他轉告我,把那首詩謄抄給他,可以在副刊上登一下。
那是我發表的處女作。我心中感謝王叔,卻還是很畏懼他,要不要打招呼這件事,比以前更加困擾我,但無疑,我寫作的熱情提高了,開始在閒暇時寫點自己想寫的東西。
有一次,我寫了一篇對於三十歲的嚮往,以我如今四十歲的高齡,看三十歲的姑娘都是少女,但在我十四歲的時候,卻覺得三十歲的女人,已經飽經滄桑,只是那滄桑是美麗的,因此讓我嚮往。
我爸作為第一讀者讀完,完全找不到北,只好又拿去給王叔看。在我爸回來之前,我心裡一直是忐忑的,我想他會怎麼說呢?矯情?無病呻吟?大人不會懂這種感受,何況,我自己也覺得,我有意無意地將某種情緒放大了。
我爸很快就回來了,讓我跟他一塊兒去王叔家。當著我的面,王叔嘲笑了我爸審美落伍,說他不能看懂這種文字裡的“情懷”,又從書架上取下幾本書,讓我拿回去看看,其中有兩本是三毛的,還有一本都德的《磨坊筆記》。
像是一個新世界就此打開,我的閱讀和寫作,進入了一種全新的狀態,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那些不易出口的心事,言過其實的情緒,以及突兀得不合乎語法的表達,王叔都能看出好處來。有的,他還會拿去發在報紙上。
此外,王叔還有一種讀書人罕見的慷慨,經常把自己才買的書借給我看。我最初看到《文化苦旅》,便是在他這裡,雖然如今的餘秋雨毀譽參半,但在當時,在國內的散文家裡,的確無有出其右者。
即使到今天,我仍然願意把《文化苦旅》推薦給中學生,他的某些姿態的確是裝了點,但對於年輕人來說,有許多情懷,是先從“裝”開始的,裝著裝著就成真的了。就像當年我們讀《紅樓夢》,一大半興趣來自於可以將自己代入成林黛玉,不管怎樣,先進去就好,總是要有進得去出得來這樣一個過程。
有時,王叔也不是很認真地薦書,但三言兩語中就能讓我有種領悟。比如他說杜甫好,我原本是喜歡王維和李白更多一點的,對於杜甫,只知道《石壕吏》這些政治正確的“史詩”,但王叔將“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隨口一念,我也頓感驚心。
如今想來,並非是王叔念得有多好,而是,相對於課本,我對他的信任度高得太多,那種信任,還原了被課本遮罩掉的杜甫的好,我後來又將杜甫許多詩句讀進了心裡,到現在,他都是我最愛的詩人。
王叔也跟我說魯迅好,也是隨口念出幾個句子,我曾經有口無心地背下來的句子,被他念出了奇妙的質感,我再去看魯迅的文字,果然如香菱學詩所形容的,仿佛舌尖上有個幾千斤重的橄欖。有一段時間,我讀魯迅讀得如醉如癡,如今看魯迅,不再全盤接受,但我依然愛他金鉤鐵畫般的文字,感謝王叔,讓我早早感受到那種美。
太和的作者苗秀俠,就很羡慕我這種近水樓臺,雖然,她同樣受益不少。
我見到苗秀俠是在某天晚上,王叔親自過來喊我,說,苗秀俠來了,你來見一見吧。
我知道苗秀俠這名字。她原本是太和縣的一個農村姑娘,天生靈氣,一邊務農一邊寫稿,被王叔從無數作者中發現,極為激賞。他才不在乎發稿節奏什麼的,有段時間,幾乎天天有她的稿件見報。在當時,地方報紙副刊的影響力驚人,連地委書記都注意到這個“會寫”的女孩子,特地坐了車去看她,還幫她解決了工作。
那晚出現在我眼前的苗秀俠,相貌與笑容都很樸實,和我見過的其他村姑並無太大差別,只是一談到閱讀和寫作,她的眼睛裡立即呈現出某種光彩。她羡慕我住在王叔家隔壁,說:“如果是我,我不睡覺也要把那些書全看完,王老師信裡提到的很多書,我們那小地方都買不到。”
“能看書多好啊”,她抬起頭,望著天花板說。我能夠想像這句話背後的內容,能看書,就能最大限度地打開自己的七情六欲,現實退場,幻象自動浮現。那時還不流行“穿越”這個詞,閱讀,卻能讓我們不依靠任何裝備,就從當下,穿越到想去的地方。
這,或者是王叔對於我們最大的幫助,他教會我們自在地寫,也教會我們把時間放在讀什麼上。我再大一點的時候,他又對我說,不要再讀三毛了,其實她有一點矯情。他交給我的書,是《異端的權利》和《人類的星群閃耀時》。有時,他也會把最新出的《讀書》交給我,說裡面有篇什麼什麼文章,你可以看看。
他不只是這樣待我,那幾年,小城裡但凡寫得好一些的作者,都會被他所注意,我常常會聽他愉快地說起,誰誰寫得不錯,雖然俗了一點,但那種俗有俗的好;誰誰讀書很多,筆法艱澀,但像書法裡的枯筆,也是一種美。他的那種孜孜然,超出了一個編輯的本分,我不知道,是什麼,讓他樂此不疲。下面縣市的作者經過小城時,甚至都住在他家裡。
但他對我和苗秀俠,又是不同的。苗秀俠後來嫁到南方,任性地放棄工作,幾年後,她攜夫君歸來,想在小城找份工作,王叔十分上心,與其他朋友合力,幫苗秀俠落下了腳。而我,在1999年底,感覺很難在合肥生存下去,給王叔打電話,想回小城到他手下謀個生計——他時任某週刊總編,卻很堅決地說,你不要回來,你回來幹嘛?
在當時,我是有點怨艾的。數年後,才覺出他的用心良苦,我與苗秀俠不同,苗秀俠拖家帶口,有個地方容身是當務之急,我隻身一人,為什麼不走得更遠一點呢?我感謝他當時堅定的拒絕。
這幾年,我跟王叔見面不多,他偶爾會發來郵件,跟我推薦,某個作者不錯,你可以關注一下,有時,還會轉一些文章給我。我一向很頭疼親朋好友轉稿,大多都寫得很可怕,唯有王叔不同,那些作者都不與他沾親帶故,他是真的覺得好。
還有一次,他途經我家,同行者為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姑娘,他說這小姑娘擅長寫劇本,他帶他們去找他的一個同學,看看能否有更多機會。我心中失笑,在這個女孩身上,我看到當年的自己。
有次參加省作協會,來自於吾鄉的幾位作家,大多都曾得王叔指教,在我們那個小小的城裡,他算得上一位燃燈者。我不知道,是什麼,讓看上去疏淡的他,有這樣一份熱情,在這樣的時代裡,他的熱情,甚至有一種古意。
我慶幸我在那條巷子裡遇見王叔,在人的一生中,有許多次遇見,遇到友誼,遇到愛,遇到懂得,遇到崇拜……遇到一個領路人尤其重要。
在如吸墨紙一般,隨便吸收個什麼就能暈染得一塌糊塗的年紀,遇到一個有水準可信任而且還助人為樂的人是多麼好,他讀過的書,走過的路,看過的雲,起伏過的心思,都有可能成為你的某個起點,你一下子就站到那裡,然後走下去。
而王叔最讓我敬重的地方是,他總希望,有一些人,能走得比他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