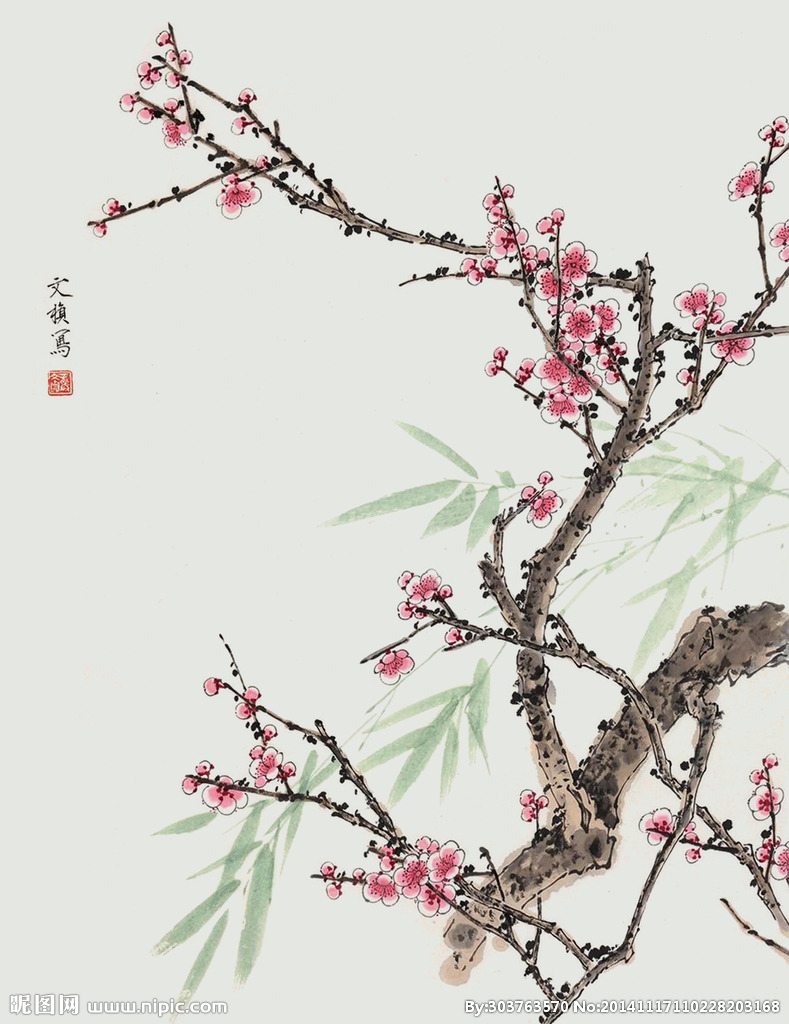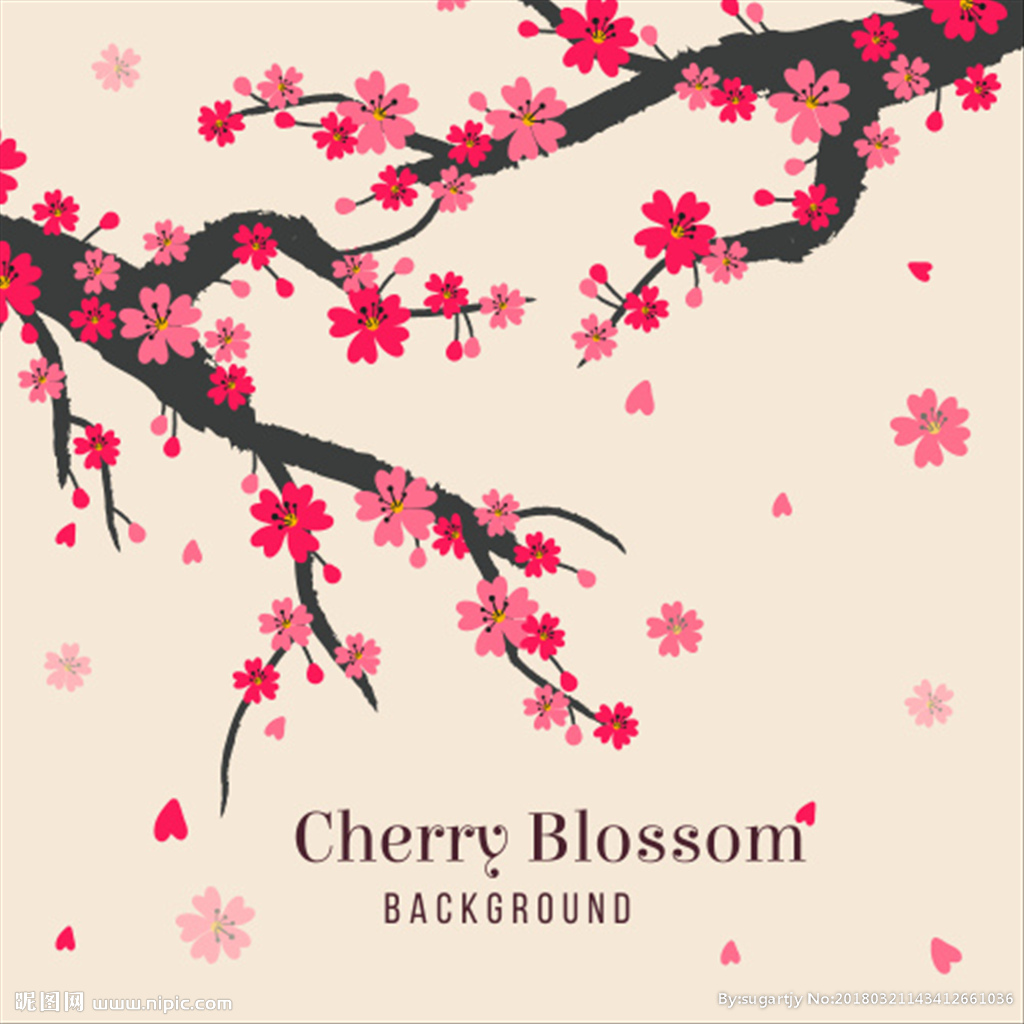夢斷梅嶺(劉秉臣)
劉秉臣先生撰 2012/07/24 12:24
李常生再序
劉秉臣先生,回族人,今年八十一歲了,曾參加過韓戰等戰役,喜好文藝創作,寄給我幾篇作品,讀後深受感動。是戰爭讓許多家庭破碎,是政客為了奪權、霸權而發起戰爭,所推動的愛國運動,都只是在玩弄可憐、無知的老百姓。我將試著將劉秉臣先生的文稿刊載於台灣或其他海外的媒體中。
也想到寄給您看看!為中國近兩百年的災難而感到無奈,也希望自由、民主、法治的火能盡快佈滿神州大地,讓荒謬的戰爭不在為野心政客們操弄服務。
2021/10/19 台北寓
夢斷梅嶺—劉秉臣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汪山、梅嶺。
仲夏,黃昏。
夕陽漸漸西沉,絢麗的晚霞輝映著蒼翠蔥郁的汪山,如詩如畫,依稀兒時熟悉的情景。多少個這樣的傍晚,我曾無憂無慮地躺在綠茵茵的草地上,嘴裡含著一根還散發著泥土芳香的野草,悠然自得地仰望著西下的夕陽和繽紛瑰麗的晚霞,小小的腦袋裡編織著未來人生的夢幻——像晚霞那樣彩色美麗的夢,直到由梅嶺傳來二姐那尖亮、悠長,響徹汪山的喊聲:「五……娃……子,回來宵夜囉!」才打斷了我的夢,悻悻地爬起來,拍拍滿身的泥土和草屑,三步並做兩步地往回跑。
浮生若夢,往事如煙,物移星換,滄海桑田。沒想到舊地重遊,已是半個世紀之後。
飄泊江湖數十秋,歸來已白少年頭。
雖然青山依舊在,但夕陽已不復兒時所記憶的那樣溫暖、壯麗、輝煌,卻宛如馬鳴風嘯的大漠落日般的蒼涼、落寞、悲壯,也許這正是我歷盡滄桑走向人生旅程最後歸宿的寫照。
夕陽用她最後的光輝和溫暖擁抱大地後,終於緩緩地沉沒,只留下我熟悉的那些山嶺——多少年來,無論在湘西剿匪的崇山峻嶺,在硝煙彌漫的朝鮮戰場,抑或在東京銀座繁華的街頭,在景色如畫的塞納河畔,我魂牽夢縈的梅嶺、老鷹嘴、張家坡、丁家寨……在蒼茫的暮色中,依然默默而忠實地屹立著,敞開他們寬闊、深厚而堅實的胸膛,迎接我和我的兄妹們——漂泊異鄉的遊子,回到他們的身旁。
夜深、山靜、露重。
月上西天。清冷的月光,給梅嶺披上了一層朦朦朧朧的輕紗,遮掩住了歷經半個世紀滄桑而荒蕪破敗的斑斑傷痕。站在昔日汪家花園那棵老銀杏樹旁,深情地凝望著梅嶺那熟悉而蒼老的輪廓,勾起了兒時那些混合著甜蜜、溫馨而又略帶苦澀的回憶,耳畔似乎又迴響起兄弟姊妹們坐在梅嶺廳前石階上,動情地合唱德沃夏克的名曲《念故鄉》,那優美而又傷感的歌聲:
「念故鄉,念故鄉,故鄉真可愛。天甚清,風甚涼,鄉愁陣陣來。故鄉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鄉,一孤客,寂寞又淒涼。我願意回故鄉,重尋舊生活。眾兄妹聚一堂,同享從前樂……」
梅嶺非我們生育之地,但在我們兄妹心中,卻有著很重很重的分量。無論是在燃遍抗日烽火的那些年代,抑或進入白髮蒼蒼的垂暮之年;無論是遠走北京、南京,抑或是客居蕪湖、上海,每當月明之夜,在天南海北的兄妹們都會情不自禁的從這首飽含滄桑感的旋律中,追憶我們失落了的童年和青春,刻骨銘心的思念我們的故居——汪山梅嶺。
我們童稚的足趾,曾親吻過這山山嶺嶺的每一寸土地,哥哥姐姐們在這裡度過美好浪漫的青春。這裡有著我們兄妹許多共同的樂趣與無窮的回憶,清水溪的流水,大堰塘的碧波,老鷹嘴的奇峰,張家坡的松濤,春天滿山遍野的映山紅,夏天燦爛盛開的薔薇、玫瑰,秋天香飄十里的丹桂,冬天,啊!梅嶺那一樹樹姹紫嫣紅令人心醉神迷的紅梅綠梅……
月圓伴著月缺,花開終會花謝,有聚也必有散。梅嶺也是我們兄弟姊妹揮淚相別,踏上各自人生旅途的起點。老鷹嘴的松濤為我們低唱離別的驪歌,清水溪的流水是我們人生壯行的酒。哥姐喲!下了張家坡,且莫再回頭,浮雲遮住了歸途,紅梅已凋零枝頭。這是命運的安排,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和自由。此一別,萍蹤寄跡,天各一方,月缺花殘,雲山夢斷,再相見不知何月何年?
兒時,我常騎坐在梅嶺庭園前的石欄杆上,搖晃著兩條小腿,好奇的遙望著對面那些綿延起伏直到遙遠天邊的群山,絞盡腦汁苦苦地思索,這些山究竟有多長多遠?山那邊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終於有那麼一天,命運也把我召喚,像先行的哥哥姐姐們一樣,背起簡單的行囊,告別梅嶺、汪山,也告別了無憂無慮的童年,爬過了一道坡又一條坎,翻過了一座嶺又一座山,開始了沒有歸程只有無盡的黎明與黃昏的人生旅程。
世事漫隨流水,歎人生幾番離合便成遲暮。
梅嶺的紅梅,多少度開了又謝,謝了又開,我們在人生路上已蹣跚跋涉了大半個世紀,有的背井離鄉數十載,兄弟相別也已數十秋。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客居它鄉的兄妹,垂暮之年鄉情親情倍增,午夜夢迴,枕有淚痕,多麼想在走完人生最後歸宿前,能再看看汪山的日出日落以及嘉陵江的帆影水波,乃數度相約結伴同歸故居。西元一九九二年秋,年屆七十四歲高齡體弱多病的大姐,率同蕪湖、北京、上海、成都的弟妹回到重慶。感謝真主,終於一了爹媽兩位老人家的遺願,圓了劉氏家族幾十年來的大團圓之夢,爹、媽、二哥和小七弟如能得知,當會含笑九泉。
「白首相逢戰爭後,青春已過亂離中。」
還記得那首我們曾多次唱過的《憶江南》吧:
「我家在江南,門前的小河繞過青山。在那花繁綠葉的村莊,我懂得怎樣笑怎樣歌唱。啊,江南!春二三月,鶯飛草長,牧女的春戀,在草原蕩漾……啊,江南,千遍萬遍唱不盡我的懷想。別離時,我們都還青春年少,再見時又將是何等模樣?!」
是啊!別離時我們都還青春年少,再見時呢?!「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歲月已悄悄流逝了五十年,我們也泰半步入花甲古稀之年。
應世端兄的熱情邀請,我們於九二年秋與九四年仲夏兩度重登汪山,在世端兄劫後倖存的舊居小住數日。一次又一次的漫步梅嶺、汪家花園、草壩子、梅花山、俄國大使館、桂花灣、老鷹嘴、張家灣、大堰塘、爛田灣、生伯世、汪山小學、伴松園……,循著當年的足跡,追憶如煙的往事,緬懷已經消逝了的歲月。我們也是在告別一個時代,一個曾經屬於我們但已經過去了的時代。
一抹如血的殘陽,照著梅嶺破舊凋零的屋面和門窗,在仲夏的傍晚,我們卻感到深秋的落寞和蒼涼,相對無言,黯然神傷,一種揪心的無可奈何的悲愴。
生活像一本打開的書,終會翻到最後一頁的。屬於我們生活的這本書,已剩下為數不多的最後幾頁了。我們兄妹都是微不足道的升斗小民,千秋功罪無人予以評說,歷史也不會對我們作出什麼結論。我們只能自己默默地與往事乾杯,在我們人生旅途的起點站——梅嶺,回首我們一生走過的路程。
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
從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到世紀末的九十年代中期,我們經歷了新舊兩個社會,兩個歷史時代,走過的是一條荊棘叢生,坎坷而漫長的路程。
為了中華民族的崛起,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我們都以不同方式參加黨領導的反對黑暗統治的鬥爭,爹雖是個商人,卻不止一次接濟、掩護地下黨的同志安全脫身,奔赴延安(有的在解放後成為相當一級的領導人)。上海解放前夕,二哥在復旦大學積極組織學生運動,被國民黨特務抓進監獄,九死一生。有的兄妹,弱冠戎伍,轉戰南北,血染疆場。建國後的幾十年裡,我們都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的勞動、工作,獻出了我們的青春和整個一生。我們的生活中有過明媚的春天,燦爛的陽光,成功的喜悅、歡樂和幸福。但卻又遭受到那麼多的打擊、挫折和不公平的待遇,為什麼我們活得那麼累,那種從心靈深處流淌出的無可奈何的累。生活教會了我們思索,我們不得不掘開歷史的斷層,對歷史進行也許是痛苦的反思,人總不能一輩子糊裡糊塗的活著。
車爾尼雪夫斯基曾有一句名言:「沒有痙攣,歷史就永遠不能前進一步。」但是每次歷史的痙攣,受苦受難的卻總是小老百姓,而歷史的痙攣又總是離不開政治鬥爭。這些年來,對這些撲朔迷離、波雲詭譎的政治鬥爭,我們還顯得太幼稚太單純,我們的忠誠裡有著盲目,我們的信任過於天真。在那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中,我們也不由自主地被捲入,狂熱的呼喊口號,義憤填膺地聲討那些揪出的所謂「階級敵人」。但是一轉眼,我們自己也成了那些政治野心家祭壇上的犧牲品,我們的政治熱情和信任,被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掮客政治騙子們利用,拍賣殆盡,只剩下至今理不順、說不清、道不明的無盡迷惘與困惑,以及沖不淨抹不平的傷痕。二哥秉鈞,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當年沒犧牲在敵人的監獄裡,勝利後,卻倒在「自己同志」的暗箭下。我們不得不以自己的鮮血來祭奠自己開創的江山,這是一場真正的「史無前例」的歷史悲劇和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
歷史有時是一面蒙了塵埃的鏡子,需要用時間去擦拭乾淨。
歷史也是生與死的銜接,新與舊的交替。我們這一代已經走下歷史舞臺,在我們的人生帷幕最後降落前,把我們對往昔歲月的回憶留駐下來,使後來者能從這些點滴的回憶中,暸解你們的父輩是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
我們兄妹中沒有權勢顯赫的達官貴人,「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大腕大亨,我們是一群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我們也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英雄業績,而是平平淡淡的度過一生,但我們活得光明磊落,乾乾淨淨,你們在流行歌曲中不是也唱只有「平平淡淡,從從容容才是真。」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可改變的執著和追求,雖然養育我們的這塊黃土地,曾經把我們青少年時代的夢、中壯年時代的追求如何揉得粉粹,滲進了我們多少痛苦的淚水,但我們還是難以離捨,在祖先留下的這塊現在還很貧瘠的土地上墾荒播種耕耘,與千千萬萬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一道,支撐著共和國大廈,為你們鋪砌通向明天的路基。我們一生也曾經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有過許多遺憾和委曲,但是面對生活,面對歷史,面對你們,我們還是能夠問心無愧地說:我們總算還能笑傲歲月,仰、無愧於天,俯、無祚於地,無悔,總算沒有白活。
晚霞和朝陽是我們兩代人生命歷程的象徵,但是沒有一片晚霞會孤獨地沉淪而不托起一輪新的朝陽。
孩子們,我們終將離去。
明天是屬於你們的。
當新世紀的曙光降臨時,但願你們能把我們的問候帶給梅嶺,替我們再看看清水溪的流水,大堰塘的碧波,梅嶺的紅梅,告慰父輩們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