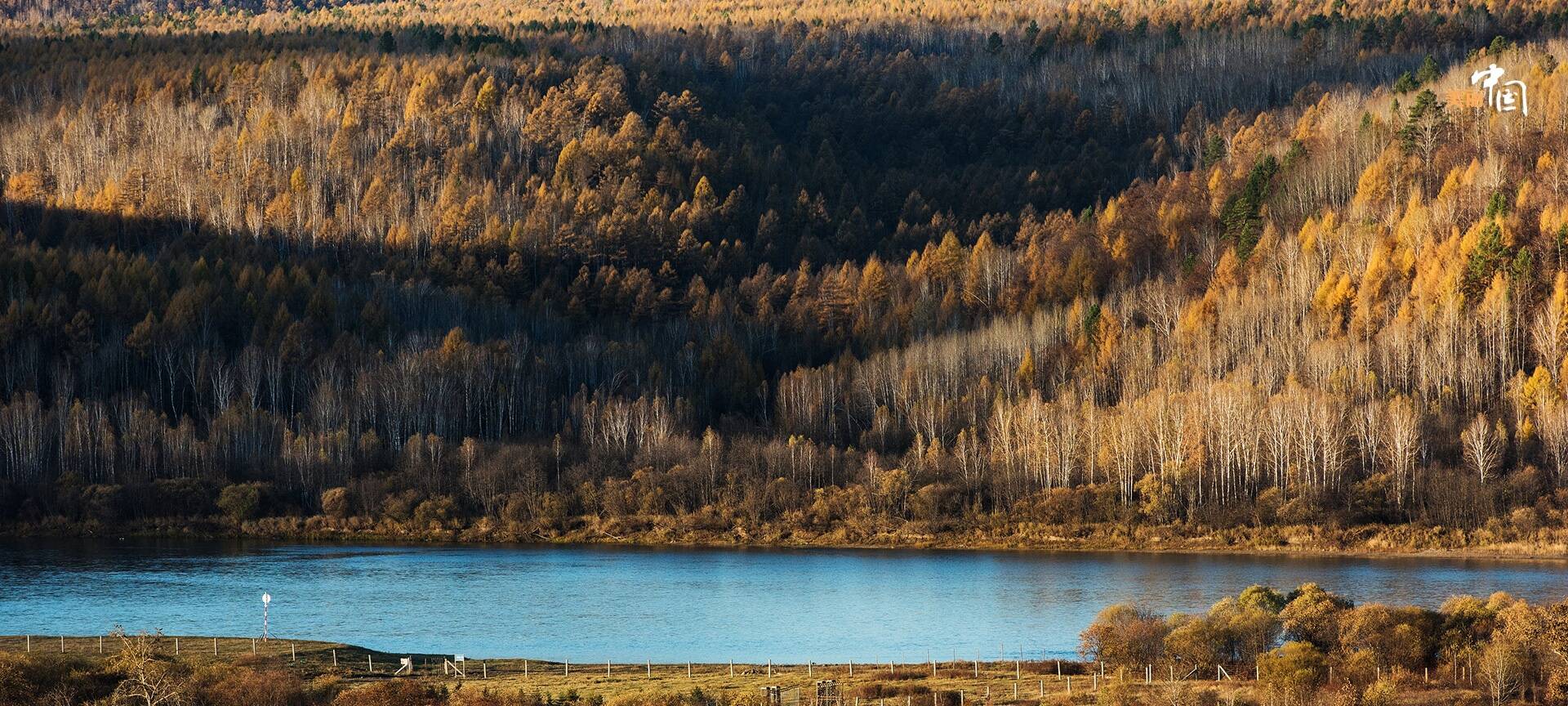聖者的使徒——記回族中醫馬牧西
于澤俊 2021/12/02刊
一.
在蘭州,馬牧西這個名字幾乎是盡人皆知。他是一位回族中醫,今年59歲,現在蘭州市永昌路中西醫結合醫院坐堂,平均每天有120多位患者慕名而來找他看病。最多的時候他一天曾接診過220多位病人。30多年來一直如此。到目前為止,他接診的人數已經超過100萬人次,這在醫學史上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古今中外幾乎沒有一位醫生能夠接診這樣多的病人。讀者不禁要問,他每天工作多久?接診120個病人,平均給每個病人看病花多少時間?是的,他給病人看病平均時間不超過五分鐘。走進馬牧西的診室你就會看到,診室一圈坐著十來個患者,他們擼胳膊挽袖子身上紮滿了銀針,馬大夫一邊給他們做針灸治療一邊在為其他患者號脈,邊號邊說方子。兩個助手為他寫方子,一個寫累了,再換另一個。替馬大夫寫方子不是件容易事,幾乎是一刻不停,這個患者剛完,另一個就接上了,不一會,寫字的手腕就酸疼起來,字也開始變形,寫不好了。很多來他這裡實習的中醫學院的學生,因為吃不了這種苦,半道就嚇跑了。在馬牧西成名之初,這些工作都是由他一個人幹的。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就碰到這樣的場面,診室門前的小院裡站滿了人,不停地往診室裡面擠,一位後擠進來的患者家屬哀求著說:“求求你,馬大夫,我屋裡的病得實在不行了,你再給加一個號吧!”馬大夫伸出彎曲的手指,說:“我實在是沒法再加了。求求你,明天早上再來吧,我的手已經成雞爪子了,藥方都開不了了。”當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馬大夫從早晨七點開始就坐在這裡,已經13個小時沒離開了。
我初次認識馬牧西是作為患者家屬。1988年,我愛人患了急性腎炎,之後轉為腎病綜合症,先後在蘭石廠醫院、甘肅省人民醫院、蘭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省中醫院就診、住院、治療,這些醫院都是甘肅最有名的醫院,到1989年,先後住了11個月的醫院,病情沒有絲毫好轉。一般腎炎病人,用激素可以暫時控制尿蛋白流失,但是激素在我愛人身上絲毫不起作用,每天劑量用到60毫克,尿蛋白仍是四個+號,化療、放療都試過了,頭髮掉光了,病情依然沒有任何起色,渾身浮腫,腫得手腕子裂開了口子,滲出了血珠。醫生不得已,給她用利尿藥,24小時內居然尿出了九公斤。當時我愛人對於治療已經喪失了信心,張口閉口就要給我交代後事,我說,你放心,我就是自學中醫也要把你的病治好。我開始到處為她尋找偏方,只要一聽到哪裡有治腎病的偏方,登上火車就走,這些偏方不但沒有治好我愛人的病,病情反而越來越重了。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我帶著愛人來到了馬牧西的診室。馬大夫見我愛人情緒低沉,號過脈開了方子之後,對我說,“這五副藥吃完尿蛋白就減到兩個+號了,不信你帶她去醫院化驗一下試試。”當時我根本不相信,因為在此之前我愛人已經吃過150多副省內幾位名老中醫的藥了,沒有任何效果。吃完這五副藥,我們又來找馬大夫,馬大夫問,去化驗了沒有?我說沒有。馬大夫說,這次吃完你去化驗一下試試。吃到第九副藥的時候,我拿著妻子的尿樣到省人民醫院化驗了一下,尿蛋白果真成了兩個+號。那是我愛人的病起死回生的轉捩點。也許是精神的力量,第一次去馬牧西的診室,我愛人行走都有困難,我專門向單位要了車,是我的一個同事和我一起架著她走進診室的。十副藥之後,她已經能夠自己走動了。我用自行車帶她去診室,她可以自己上車。後來,她的病徹底治好了,上班了,中間雖有種種反復,都不是醫藥能夠解決問題的。這裡要告訴讀者的是,我愛人現在依然健康地活著,她已經退休了,每天在家為我洗衣做飯。
二.
中醫看病靠的是望、聞、問、切,其中最關鍵的是切脈。一個優秀的中醫可以做到“病家不用開口,便知病情根源”。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中西醫結合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中醫也越來越多地依靠化驗、X光透視、CT、超聲波、核磁共振等西醫檢測手段檢測病情,這樣無疑增加了診斷的準確性,但是隨之中醫也在退化,越來越多的中醫學院的學生已經不會切脈,而更多地依靠西醫檢測手段。馬牧西卻不是這樣,他的診斷還是靠三個指頭。我愛人第一次到他那裡就診,他號完脈說,你是左腎疼右腎不疼,這一語中的的結論讓我和我愛人都很吃驚,這和西醫檢查的結果以及我愛人自己的感覺完全一致。
和我愛人一起去找馬牧西看病的還有兩位朋友,一位是蘭州大學的女團委書記孫朝暉,給我愛人看完之後,馬大夫摸了摸孫朝暉的脈搏,張口便說:“你是想兒子了。”一句話說得孫朝暉臉一紅,因為她結婚幾年了,一直沒有孩子。馬大夫給她開了一個方子,吃了不久她就懷孕了,現在孫朝暉的女兒已經大學畢業了。另一位是甘肅的著名作家張俊彪,他患的也是腎病,尿血,開始是兩個+號,後來是四個+號,去馬大夫那裡的時候,用他自己的話說,已經滿視野都是了。馬大夫號完脈之後說,你的病主要是肝上的問題,腎的問題在其次。張俊彪大吃一驚。他和我愛人一樣,也跑過很多家醫院治療,還專門到北京、天津的大醫院看過,醫生一直是按腎病給他治的。當時他的病情已經十分危險,如果不是碰到馬大夫,疾病很可能會奪去這樣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的生命。張俊彪病好之後調到了深圳,一直擔任深圳市作協主席至退休。
馬大夫號脈的功夫有如神助,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專門在馬大夫的診室待了一天,觀察他怎樣號脈看病。不一會,進來一位患者,馬大夫一搭脈搏張口便說,你的血壓是90——140,那位患者說:“我早晨剛剛量過,是100——140”,馬大夫說,“現在是90——140 。不信咱們找個血壓計量一量。”恰好患者中有一位帶了腕式血壓計,伸手遞了過來,“看看馬大夫說的准不准?”那位患者戴上血壓計一量,果真是90——140 ,診室裡立刻一片喧嘩,簡直太神了!另一位患者坐下,馬大夫把手往他脈搏上一搭,說:“你的膽沒了。”患者說,是的,前不久患膽結石,手術時摘除了。
馬大夫號脈,不僅能準確地說出病情病因,甚至能號出許多與病情無直接關係的身體症狀。一位回民婦女來找馬大夫看病,馬大夫邊號脈邊說:“你超生了。”
那位婦女不好意思地反問道:“你咋知道呢?”
馬大夫笑著說:“我咋不知道?你已經懷了五次孕,生過三個娃娃了。”
諸如此類的事情,經常讓患者驚歎不已,諸如頭一天喝了酒,吃過洋芋、粉條之類的生活細節,他也都能從脈象上看出來。一位患者吃著中藥還在喝酒,馬大夫很生氣,說:“你這樣子怎麼能指望病情好轉?”患者矢口否認,說他沒喝酒,馬大夫說:“算了吧,你昨晚上至少喝了半斤。”那位患者低頭不語。
馬大夫不僅脈功好,針灸功夫也不錯,他每天從早到晚給人號脈開方子,也從早到晚給人扎針,他的診室外面是排隊等候叫號的,裡面坐的幾乎全是針灸治療的病人。一批到時間走了,再換一批,直到診室下班了,還有最後一批患者坐在那裡等著拔針。
除了湯藥和針灸,馬大夫還自製了不少藥丸、藥片、藥水,用以輔助治療。有一年夏天,我的肝區疼得很厲害,到醫院檢查,查不出病因,醫生也沒法採取措施。我心裡很害怕,擔心會不會長什麼東西,便來找馬大夫。馬大夫用紙包包了三片藥給我,藥片是土黃色的,有一分錢硬幣那麼大,馬大夫說,回去吃了就不疼了。我問馬大夫是什麼病,馬大夫說,按西醫的說法,應該是肝神經疼。後來我問一些西醫朋友,他們說根本沒聽說過有什麼肝神經疼。第二年夏天我又患了急腹症,腹部莫名其妙地疼痛,既不是胃疼,也沒有腹瀉等腸胃方面的炎症,但是疼得直不起腰來,馬大夫也是用幾粒藥片就把疼痛止住了。我的一位北京的朋友,腿上患皮膚病,痛癢難熬,多年醫治無效,聽說馬大夫能治各種疑難病,便專程跑到蘭州來找馬牧西。馬大夫給了他一瓶自製的藥水,擦了不到一星期皮膚症狀就完全消失了。
在馬大夫的診室裡、家裡,窗臺上、牆根下到處擺著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裡面泡著各種各樣的中草藥,那都是他自製的藥物,這些藥不知治好了多少疑難病症。
馬大夫在行醫中,對各種偏方也不拒絕,有許多奇怪的偏方是出自他的手,例如,一位病人患膝蓋水腫,馬大夫在開藥治療的同時,讓患者用豆腐敷膝蓋,患者說效果很好;一位滿臉長滿青春痘的小姑娘,馬大夫在開藥治療的同時,讓她把黃瓜搗成泥敷在臉上,當她第二次來複診時,痘痘不見了,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去年9月,我患了神經性耳鳴,跑遍北京各大醫院,吃過中藥,做過針灸治療,都沒什麼效果,醫生說這個病很難治,神經性耳鳴和神經性耳聾是親兄弟,得了神經性耳鳴,十有八九會導致耳聾,有的醫生直言不諱地告訴我,這個病遲早是聾,你就等著聾吧,聾了就好了,對身體也沒什麼影響。我不甘心,打電話給遠在蘭州(此時我已調北京工作)的馬大夫,馬大夫在電話上聽我說了說症狀,不一會,開了一個方子,用短信發了過來,我按照馬大夫的囑咐,吃了七副藥,起色不大,又打電話給馬大夫,問這個病有治沒治,馬大夫堅定不移地說,有治,你放心吃藥,這個方子再吃七副,吃完我再給你換個方子。如果治不好,我坐飛機到北京來給你治。我又吃了七副藥,之後馬大夫換了方子,第二個方子只吃了四副,我就有點沒信心了。此時剛好有個到成都出差的機會,我對單位領導說,出完差我要拐彎到蘭州去一趟,看看病。我想讓馬大夫當面號號脈,再換個方子試試,誰知到成都待了兩天,耳朵居然不響了。到了蘭州以後,我對馬大夫說,出來的時候是找你看病來了,現在是給你報喜來了。
在治療我的耳疾的時候,馬大夫還用了一個偏方,讓我晚上睡覺時在耳庭裡放兩片蔥白,我立刻想到耳聰目明這個成語,覺得有點搞笑,心想這是什麼偏方,純粹是心理安慰。事後回想起來,這個偏方也不是沒有道理。當時耳鳴嚴重,像鴿哨一樣從早到晚不停地響,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耳朵上,搞得精神很緊張,耳朵總是熱烘烘的像火燒一樣,貼上蔥白以後,立刻覺得十分涼爽舒適,不那麼難受了,我猜想貼蔥白不光是心理療法,也是減輕病人痛苦的一種辦法,大概貼黃瓜片、蘿蔔片也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貼蔥白不過是要用耳聰這個諧音,顯得更吉利,更容易對患者起到安慰作用。
三.
我認識馬牧西是在25年前,那時他剛剛三十出頭,個子將近一米八,身材魁梧,儀錶堂堂,寬額頭,深眼窩,大鼻子,下巴微微向前撅,明顯帶有西方人的血統,皮膚白皙、細膩得像個大姑娘,氣色紅潤,氣質上又像個能征善戰的將軍。眉宇間透著一股高貴之氣,使我一下子聯想到西方影視戲劇中那些王子的形象。中國民間歷來有一種說法,大夫的精氣神旺,才能鎮得住藥,像馬牧西這樣的氣質,估計所有的藥神、藥鬼們都得臣服。
在馬牧西的診室和診所走廊的牆上,到處貼滿了人們送來的感謝信、表揚信、錦旗和牌匾,上面寫著“妙手回春”、“手到病除”、“華佗再世”、“德昭技高”、“大醫精誠”、“懸壺濟世”等讚譽之詞,有的乾脆稱他為“神醫”。還有許多在他這裡看過病的書法家、藝術家的書畫作品和題字。記得有“杏林三月茂,人間四時春”、“梅花香自苦寒來”等。這些錦旗、牌匾、字畫每隔一段時間就換一次,因為不斷有新治癒的患者往這裡送。馬牧西並不希望這樣,但是診所要宣傳自己、擴大影響,馬牧西也不好反對,於是,他在那些牌匾中間掛上了一塊大大的他自己定做的牌匾——來者吾師。
如今馬牧西已經是譽滿金城(蘭州別稱),家喻戶曉,但是,走到今天這一步,他卻經歷了無數的艱辛。
馬牧西沒有上過大學,他是自學成才的。馬牧西的父親是中醫,在他的家鄉臨夏一帶很有名,曾經治好過無數疑難病症,深受廣大穆斯林和各族百姓們的愛戴。馬牧西小的時候,看著父親給人號脈覺得好奇,也裝模作樣地去給人號脈,號完之後總是一個結論:脈搏跳動尚有力。有心的父親並沒有把這當做孩子的遊戲,而是認認真真地教他背湯頭歌訣,可是小孩子對那些枯燥的藥名不感興趣,他只對號脈感興趣,讓父親教他號脈,父親說,你不要急著學號脈,等基礎打扎實了,我自然會教你。誰知他自己邊看邊摸索,很快就掌握了號脈的基本功。有時患者慕名而來找他父親看病,父親不在家,馬牧西便伸手去給病人號脈,居然能說個八九不離十。父親發現後,嚴厲禁止他這樣做。父親的禁令依然阻擋不住一個孩子的好奇心,上學的時候,閒暇時間他依然會給同學們號脈玩耍,而且說中過不少同學潛藏的病症。中學時代的馬牧西,在同學中已經小有名氣,同學們毫不懷疑,馬牧西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好中醫。
遺憾的是,馬牧西沒能考上大學。這不能全怪他,五十年代出生的這批人,正趕上文化大革命,中小學就沒有正經上過幾天課,加上邊遠地區教育條件差,絕大多數孩子是不可能有上大學的機會的。馬牧西也不例外。中學畢業後,他在家待業沒事幹,開始刻苦鑽研中醫,把父親讀過的中醫典籍基本上都讀遍了,他聽父親說過,《黃帝內經》是中醫的核心經典,便開始苦讀《內經》,很快便把《內經》背會了。馬牧西的記憶力極強,凡是在他那裡看過病的人,第二次來找他,哪怕時隔多年,他都能叫出對方的名字。《內經》攻下來之後,其他中醫典籍對他來說就容易得多了,那些湯頭歌訣,他在不經意間已經爛熟於胸了。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有人求上門來,馬牧西已經可以代替父親給人診病開方了,父親發現以後,再次對他發了火:你既無學歷又無行醫資格,怎麼能隨便給人開方子?
1974年,馬牧西下鄉插隊,在公社合作醫療站擔任赤腳醫生,已經能夠用中醫方法治療各種常見病、多發病。他邊實踐邊學習,醫術有了很大提高。兩年後,他被招工招到了省建六公司。馬牧西已經深深地愛上了中醫這一行,他一面利用業餘時間刻苦鑽研中醫典籍,一面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實踐所學到中醫理論。工友們有個頭疼腦熱,他便伸手去給他們號脈,告訴他們該吃什麼藥,採取哪些治療措施,漸漸地,馬牧西在建築工地上出了名,有病沒病的工友們都來找他號脈,有的是看病,有的想看看自己的身體狀況,有的純粹是出於好奇,來看看他號脈號得究竟准不准。在這種半工半醫的過程中,馬牧西的脈功有了長足的長進,已經能夠準確地診斷病情,把握分寸了。到後來,不僅工友們來找他看病,連那些工友家屬們也找上門來,經常是他正幹著活便有病人來找他,有些病人病得很厲害,馬牧西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來為他們診脈。在年輕的馬牧西腦子裡,還沒有學歷、行醫資格、法律界限這些概念,有人勸他不要亂給人看病,這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但是馬牧西心裡有數,他開出的方子絕對不會把人吃壞。在他看過的病人中,還沒有一例因為吃了他的藥而有什麼不良反應。
馬牧西的名字不脛而走,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來找他看病,也影響了他的正常工作。於是領導找他談話,既然你這麼喜歡中醫,就換個單位吧,你不喜歡這裡的工作何必在這受罪呢?那時的鐵飯碗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馬牧西一時還捨不得丟掉這份工作,但是來找他看病的人越來越多,他最終不得不辭掉了“鐵飯碗”,調到省經濟協作辦公室下設的一家半官方半民間的醫療機構:甘肅名老中醫門診部。
此時的馬牧西已經治好過不少疑難病症,在蘭州聲譽鵲起,名老中醫門診部的負責人也有所耳聞,他們願意接受馬牧西。可是馬牧西既沒有學歷也沒有行醫資格,怎麼安置他的工作?在名老中醫門診部坐堂的都是省內各中醫院退下來或即將退休的老中醫,或多或少都有點名氣,即使一點名氣沒有,至少還有個主任醫師的頭銜掛在那裡,讓馬牧西和他們一起坐堂診病顯然不太合適。於是門診部領導決定先讓馬牧西在藥房工作,然後再去疏通衛生管理部門,看能否解決他的行醫資格問題。
馬牧西一到藥房,那些慕名而來的患者便找上門來,開始是一天三個五個,後來是十個八個,馬牧西一邊抓藥一邊給他們診脈開方,誰知後來找他來看病的人越來越多,一個月以後,門診部門前來找他看病的人已經排長隊了。馬牧西的行醫資格問題還沒有解決,怎麼辦?門診部負責人請示領導,領導回答說:“改革開放時期,可以特事特辦,有些政策界限可以突破,既然他會看病,就讓他看,可以一邊坐堂一邊給他辦理行醫資格。”於是,在門診部的大堂裡,又給馬牧西加了一張桌子,這是馬牧西第一次以“合法”身份給人看病。
在馬牧西來到之前,門診部的生意一直是冷冷清清、不死不活,勉強能夠維持。馬牧西到來之後,前來就診的人越來越多,門診部的效益也越來越好。不到半年的時間,每天來找馬牧西看病的人已經超過了150人,最多的時候一天達到200多人。要掛馬牧西的號,已經不是件容易事,要麼得早起排隊,要麼就得托人。我第一次帶我愛人去看病,就是托了人去的。馬牧西是臨夏人,他剛成名的時候,從臨夏、東鄉等地慕名而來找他看病的人特別多,後來,他的名聲已經遠播全省,很多人千里迢迢從武威、張掖、酒泉、平涼等地專程跑來找他看病,面對這些父老鄉親,馬牧西一個也不忍心拒絕,只要有人找來要加號他都給加,以至於在長達五六年的時間內,他每天要工作十三四個小時。門診部早上八點上班,他七點便開始給病人看病。他初出茅廬,還沒有助手,號脈、開方都是一個人幹,那時電腦還沒普及,開方要用複寫紙,一式三份,寫字必須用足力氣,每到下午,握著圓珠筆的右手便伸展不開了。他的右手中指第一個關節,到現在還留著一個深深的窩,那是當年握圓珠筆留下的痕跡。他處理病人,就像《三國演義》中的龐統斷案一樣,眼看、耳聽、手寫、嘴發落,右手還沒寫完上一個方子,左手已經搭上了下一個患者的脈搏。馬牧西最初行醫的幾年,一直是以這樣的狀態工作著。平時有點頭疼腦熱也不得不堅持,甚至發著高燒還來上班,他不來,那一百多號病人就得等到下一天,一想到那些比他病得更厲害的人,他在家裡就躺不住了,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馬牧西除了去麥加朝覲或到外地出診,幾乎沒有缺過一天勤。
四.
自從馬牧西開始坐堂看病,門診部那些名老中醫臉面上就有點不好看了。因為每天來就診的幾乎全是找馬牧西的,其他人的號加起來不足他的十分之一,有的人坐一天也沒有一個患者掛他的號,有的病人本來是衝著名老中醫來的,但是到了門診部一看,馬牧西這麼有名氣,乾脆又改掛了馬牧西的號。於是幾位老中醫一起找門診部領導談話,質疑馬牧西的行醫資格問題,有的還向門診部提出了辭呈,既然有這麼一位赫赫有名的馬牧西,還要我們來做什麼?
為了協調馬牧西和老中醫之間的矛盾,門診部把馬牧西的診室遷到了馬路對面的一個小院子裡。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更鮮明的對比,馬路這邊,寬寬敞敞的門診大堂冷冷清清,七八位老中醫坐在那裡聊天,幾乎一個來看病的人也沒有,而馬路對面的小院子裡,從早到晚擠滿了患者和他們的家屬,有的站著,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趴在診室的窗子上張望,盼著早一點輪到自己,小院子裡站不下這麼多人,門外的馬路上都是三五成群等著叫號的,連過往的汽車到這裡都要鳴笛減速,一時成了南昌路的一道風景。終於有人按捺不住了,寫信向衛生管理部門告狀,舉報馬牧西非法行醫。接著,街頭巷尾便傳出了各種攻擊馬牧西的流言蜚語,有的說馬牧西是個騙子,有的說馬牧西膽子太大,什麼藥都敢開,多大劑量都敢用,吃了肯定要出問題。原話說得很直白,“那麼大劑量的藥是給人吃的麼?那是給牲口吃的。這樣下去不死人才怪呢。”
衛生管理部門很快便派人到門診部來進行調查。馬牧西沒有行醫資格是事實,這個狀一告即准,衛生管理部門下令取締了馬牧西的行醫資格。馬牧西又回到了藥房。但是馬牧西的大名已經傳遍金城,他在藥房抓藥,人們還是不斷找上門來請他診脈,請他開方,門診部前依然車水馬龍。馬牧西根本不能露面,一露面便被人們圍住了。門診部領導只好讓他暫時回家休息一段時間。與此同時,門診部又與衛生管理部門協商,希望給馬牧西爭取到合法行醫的資格。衛生管理部門感到很為難,一方面,攻擊馬牧西的輿論沸沸揚揚,他們不敢擔這個風險;另一方面他們也瞭解到,馬牧西確實是一位深受群眾愛戴的好醫生,取締馬牧西的行醫資格已經引起了廣大群眾特別是回族群眾的強烈不滿,經過省經協辦和衛生管理部門反復協商,最後決定讓馬牧西參加當年省衛生廳職改辦組織的職稱考試。
1992年11月4日,馬牧西順利地考取了中級職稱。現在,他可以名正言順地坐堂行醫了。馬牧西在家閒居準備考試的時候,關於他的謠言也隨之終止,可是他一出山,各種污蔑不實之詞又接踵而來,反對馬牧西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有些有閑的人就是跟他過不去,非要把他搬倒不可。有的人甚至利用關係動用了合法媒體。另一方面,來找馬牧西看病的人依然有增無減,門診部專門為他租下的那個小院子,依然是從早到晚人聲鼎沸,馬牧西根本顧不上去解釋那些流言蜚語,每天光是看病就已經耗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偶爾有些閒話傳到他的耳朵裡,他也只能苦笑著搖搖頭,實在氣不過的時候,便說一句:“我可以對每一個來這裡看病的人負法律責任,如果把病人治壞了,我情願去坐大牢。”
任何一位醫生都不可能包醫百病,有些病能治好,有些病就是華佗再世也治不好。三十年過去了,馬牧西看過的病人已經超過了100萬,他治好了無數病人,也有不少病人吃了他的藥效果不大,或者沒什麼效果,但是從來沒有一位病人因為吃了他的藥而病情加重或者留下什麼後遺症,在他行醫30多年的時間裡,沒有出過一例醫療事故,沒有和一位患者紅過臉、吵過架,也沒有任何一位患者找上門來說你把我的病治壞了。按說反對馬牧西的輿論應該自生自滅了,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三十多年來,反對馬牧西的輿論幾乎一天都沒有停止過,這也許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奇怪現象。另一個奇怪現象是,反對的呼聲這麼高,來找馬牧西看病的人數依然不減,三十多年來,幾乎沒有一天少於100人。現在來找他看病的,已經不僅僅是本省的患者和回族兄弟,而是來自全國各地,有山西、陝西的,有廣東、四川的,有新疆、雲南的,還有很多外國朋友。
五.
馬牧西的處方特點是大方子、大劑量,他的方子一般用藥都在二十味以上,多的時候能達到三十味,劑量之大,一般的藥鍋往往煮不下。攻擊他最多的也是這個問題。我就這個問題採訪過他,他說:“現在的中草藥很多是大面積種植的,為了高產,大量地使用化肥,藥效遠不及野生的。藥品市場開放以後,收購品質也大不如從前,以次充好的現象十分普遍,如果還按過去的劑量用藥,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關於大方子和小方子的問題,中醫史上一直是有爭議的,醫聖張仲景曾說過:藥過十三百病不治。但是到了唐代,孫思邈就推翻了這個結論,採用大方子。正是那些敢於突破傳統的醫生發展了中醫學,否則中醫會永遠停留在一個水準上,甚至倒退。作為初出茅廬又是這樣一位有爭議的醫生,馬牧西不敢這樣說,只能默默地做,但是我想他治好了那麼多別人治不好的病,一定是有自己獨特的思考和創造的。
馬牧西成名是因為看不孕症,不少結了婚沒孩子的婦女吃了他的藥都懷了孕,有了孩子,便一傳十、十傳百地把馬牧西的名字傳開了。實際上馬牧西最擅長的是治腸胃病、肝膽病,馬牧西所有的方子都有炒三仙,這三味藥是通腸胃的,他曾對我說,腸胃是交通要道,無論看什麼病,先要把腸胃打通,腸胃不通,什麼病也治不好。他不僅擅長腸胃病、肝膽病,治療風濕病、腰椎病、紅斑狼瘡、過敏性紫癜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戲,還治好過許多普通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奇怪怪的病症。
由於馬牧西的聲名遠播,很多高級幹部和社會名流都來找他看病,一些遠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患者或由於病重不能前來,或由於工作原因脫不開身,經常請他去出診。他曾先後給國務院副總理方毅、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楊靜仁等看過病,省軍級以上的幹部來找他(請他)看過病的不下百人,各界名流更是不計其數。馬牧西無論到哪裡出診,總是週五晚上或週六上午走,周日下午必須趕回蘭州,他心裡還惦記著每天慕名而來的那一百多名患者,如果週一早上七點他不能準時坐在診室裡,門診部就要亂套了。他曾多次到北京出診,但是從來沒有認真地遊覽過北京的名勝古跡,到現在為止,他只是對天安門有一點印象,其餘的大部分地方都沒去過,每次出診總是來去匆匆,給人看完病登上飛機就走。
是什麼力量支持他這樣做呢?是為了錢嗎?馬牧西成名以後,很多人都以為他有錢,連我也這樣認為。每天那麼多人看病,光是掛號費提成就得多少?直到去年我再次見到馬牧西才知道,三十多年來,他從沒提過一分錢的掛號費,現在每天從他手上開出的藥方價值三萬多元,一年光是中藥一項給門診部創造的利潤就多達200多萬,他也沒有從這些利潤中提取過一分錢。他的收入只是每月八千元的工資。幾年前,甘肅醫藥管理部門對於民營醫院的掛號費出臺過一個新規定,具有副主任醫師以上職稱的醫生,可以提高到30元,但是馬牧西一直壓著不讓提。馬牧西深知西北地方百姓們的窮苦,看病規,看病難,很多人來一趟不容易。以馬牧西現在的名氣,掛號費就是100元也不算高,筆者曾在北京的一家民營中醫院做過針灸治療,掛號費就是一百元,更有那些電視上炒作出來的所謂“名醫”把掛號費提到了上千元,但是馬牧西的掛號費只有五塊錢。由於馬牧西堅持不准掛號費提價,醫院一年僅在他的掛號費上的損失就是幾十萬。但是馬牧西不拿這個錢,院方也無話可說。以馬牧西現在的醫術和他為他所供職的醫院所做的貢獻,年薪百萬應該不算過分,但是他的年收入只有十萬左右。許多患者朋友知道這個情況後都為他鳴不平,動員他去找院方談判,提高工資待遇,但是馬牧西抹不開這個面子。馬牧西生就一副傲骨,也是個很有魄力的人,他的氣質讓所有的人都感到敬畏,無論是省長、市長,還是什麼明星大腕,在他面前都得畢恭畢敬,但是在個人利益上,他卻永遠都張不開口。他不愛錢,朋友們相聚,一說到他的收入太低,他總是說,我沒那麼大需求,掙那麼多錢有什麼用?
既然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眼前的利益,那麼是什麼支撐馬牧西這樣做呢?我們可以從他每天的生活中去尋找答案。馬牧西每天早晨五點多就起床做禮拜,吃過早點,七點鐘之前就趕到了診室。門診部八點鐘正式開始營業,九點多他已經看了四十個病人了。現在他有兩名助手協助開方,處理病人很快,大約在一點鐘的時候,就把120個左右的病人看完了。有時病人多一些,就要忙到兩三點鐘。現在的工作狀況比他剛成名時略微輕鬆了一些,但是連續七八個小時的工作量依然是很繁重的,工作時間經常忙得連廁所都顧不得上,直到十一點左右實在憋不住了才去一趟。午飯都是在兩點以後,下午是他的休息時間,可以喝喝茶、看看報,讀一點業務書籍。但是下班之後,手機依然不停地響,不斷地有患者或者患者家屬打來電話問這問那,也不斷地有朋友受人之托約他看病開方,所謂休息時間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馬牧西不抽煙、不喝酒、不會打牌下棋,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要堅持的是每天下午日落之前準時到清真寺去祈禱,祈求世界和平,祈求真主保佑天下蒼生都能過上幸福平安的日子。我曾問過馬牧西,祈求世界和平是常年的主題還是臨時性的,他告訴我是常年性的。馬牧西是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一年365天禮拜,從不間斷,無論颳風下雨。他是穆斯林中的傑出人物,他的一舉一動對周圍的信眾都有很大影響,因此便更加注意自己的行為,為周圍的人們做出榜樣。他曾經五次到麥加朝覲,這是一個穆斯林少有的殊榮,也是他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動力。如果要問馬牧西哪裡來的那麼大工作幹勁,我認為首先是信仰給他的力量。馬牧西成名以後,曾有不少朋友介紹他到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發展,馬牧西都婉言謝絕了。一位深圳的朋友,註冊了一家民營醫院,已經辦好了營業執照,請他去坐堂,他堅辭不肯。馬牧西的老家臨夏是回民聚居地,蘭州雖然已不是故鄉,但是在小西湖一帶仍有一個回民聚居區。西關十字有大清真寺,他家附近也有一個清真寺,早晚禮拜都很方便。離開這裡,他找不到和周圍人的共同信仰,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支柱。
二十多年前,我初識馬牧西的時候,曾建議他到北京去深造。馬牧西反應敏捷、博聞強記,以他的天資,三兩年拿下碩士、博士學位是不成問題的。馬牧西沒有聽從我的建議,他對自己的人生另有打算,他離不開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離不開時刻需要他的廣大患者。是對穆斯林兄弟姐妹、對下層勞動人民的發自內心的愛支撐他走過了這三十多年的人生道路。
馬大夫熱愛自己的職業,給人看病時,不僅充滿了對患者的愛心和同情,還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對待自己的職業的激情。在他的診室裡,我看到了這樣的情形:當他給病人號過脈摸准病情之後,總是要稍微思索一下,仿佛一個大將軍在斟酌自己的作戰方案,這個方案往往在幾秒鐘之內就形成了,然後便像炮兵開炮一樣,一口氣開出藥方:
丹參麥冬五味子枸杞子,棗仁遠志黃連夜交藤!瓜蔞!白芍枳殼青陳皮!熟地當歸大雲山萸肉水牛角……
他一口氣說完藥名,兩個助手都知道他通常用藥的劑量,一般不用問,需要特別增減劑量的,他說完藥名之後會單獨交代。在開方子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兩眼放光,格外興奮,方子開完,仿佛打完了一場硬仗,帶著滿意的笑容輕出一口氣,便又恢復了平靜。
我調離蘭州已經十年了,這十年我一直沒有見到馬牧西,去年有幸兩次見到了這位我最尊貴的朋友。十年不見,馬牧西老了許多,頭髮變得十分稀疏,快見頂了,頭上冒出了根根白髮,當年王子般的風采已經逝去,臉上平添了許多歲月留下的皺紋。我在心裡說,他老多了。看到馬牧西這個樣子,我心裡很難過。他本可以保養得很好,作為一個中醫,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身體調理得比常人更健康、更年輕,但是他常年忙於給別人看病,卻很少注意自己的健康。由於常年久坐,他患了嚴重的頸椎骨質增生、腰椎骨質增生,心血管三處狹窄,西醫建議他做支架,他沒有做,一直用中藥維持著。他的健康到這種程度,完全是累的,除了久坐之外,每天過度勞累之後,饑腸轆轆,暴食一頓午餐,也大大地損害了他的健康。見面之後,我反復告誡他要注意身體,並建議讓醫院出個通知,每天診脈時留出兩段休息時間,站起來活動一下,他笑笑說:“幾十年都這樣,改了不好,那樣患者會以為我拿架子,來看病的人心情都很急迫,就算站起來也沒法休息,看著滿走廊的病人,心放鬆不下來。”我再勸,他便說:“注意了能多活幾年?趁著身體還好,多做點有益的事等於是多活了。老了,幹不動了,你想做事也做不成了。”
我說,“你不為自己著想,也不為患者想想?難道你就不想多活幾年,多救活一些病人?”
馬牧西笑笑不再答話。我知道,我的話他根本沒聽進去。我只能在心裡默默地祝福他了。
如果讀者朋友問我,你說的都是真的嗎?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句句真實,我願對文中的每一句話負責,如果您看了這篇文章之後慕名去找馬大夫,請您見到他的時候,一定替我問聲好。
2012年11月19日草稿
2014年2月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