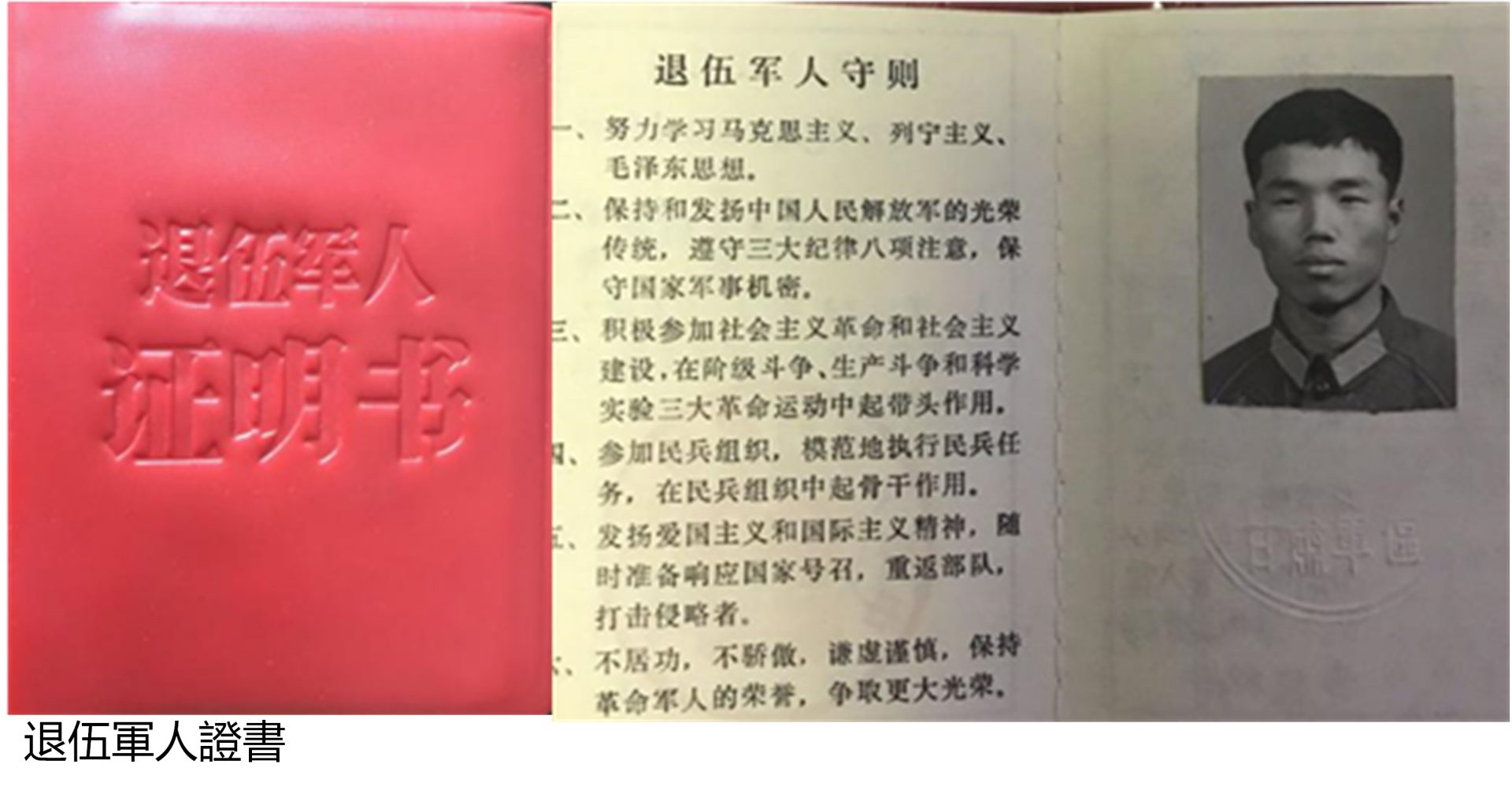我是一個兵
于澤俊 2021/12/02刊
一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個幸運兒,正當全國上山下鄉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三線建設急需補充人馬,我和一批三線職工子弟躲過了插隊,成了第四冶金建設公司的工人,那年我16歲。兩年後,年輕人那種狂熱的激情又把我捲進了部隊。那時解放軍被捧上了天,紅帽徽紅領章是每個青年崇拜的圖騰,當兵成了我夢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從士兵到將軍成了我的奮鬥目標。過去徵兵對象主要是農村青年,很少在工廠招募。那年單位偶然分到兩個名額,我才有了機會。公司裡和我有同樣想法的年輕人大有人在,報名報了兩百多。那些日子,我像打了雞血一樣,下班就往招待所跑,纏住徵兵幹部不放,終於在百分之一的幾率中勝出,如願以償。
部隊駐紮在青銅峽,西面是騰格裡沙漠,東面是號稱小江南的銀吳平原,一條鐵路給沙漠和平原劃出了分界線。營房位於路東10公里的地方,屬於小江南的住戶,來自騰格裡的沙塵暴經常越過分界線襲擊這裡的住民。
青銅峽是著名的古戰場,秦代大將蒙恬曾在這裡抵禦匈奴,楊家將在這裡打過仗,據說附近還有穆桂英的點將台,楊宗保和西夏交戰的地方就在北面不遠的賀蘭山腳下,離部隊營房只有幾十公里。
入伍後連隊對新兵進行體能和靈活度測試,一個十公里長跑把我甩出了隊伍,狼狽不堪。投彈只投了23米,不及格,羞得我無地自容。由於從小對體育不感興趣,身體十分僵硬笨拙,單杠測試直挺挺掛在杠上,像半扇待售的豬肉,怎麼也沒法把身體卷到杠上去,兩個老兵抬手把我掫了上去,頓時全身的血都湧到了頭上,下來之後吐了一地。沒想到我的體質體能這麼差!
晚上連裡教唱歌曲。副連長是全連唯一能識譜的,那天他唱錯了一個音,我多嘴說副連長你唱得不對,副連長說你來給大家教。飯廳裡立刻掌聲雷鳴,身邊的戰友連推帶搡把我推到了前面。我的臉紅到了脖子根,緊張程度不亞于白天掛在單杠上。從此我就成了連隊的歌曲教員兼指揮。
唱完歌副連長把我叫到他房間,給了我幾本小冊子,是部隊不定期發的軍旅歌曲,我說我不識譜,副連長說我教你,他給我講了半個小時怎樣識簡譜,回到宿舍我翻出一首新歌試了試,三遍之後居然能磕磕巴巴唱出來,興奮得手舞足蹈。
這點特長遠不足以彌補我對體能的自卑,軍事訓練樣樣不合格,每天收操講評被班長罵得狗血噴頭,直到第一次實彈射擊,班長才有了點好臉,八發子彈打了78環,全連第一。
部隊訓練不講科學,每天飯後要開展三五槍三五彈活動,我說這樣訓練不科學,吃完飯劇烈運動容易得胃病。班長把眼睛一瞪說,就你聰明!哪來那麼多小道理!
我知道小道理在這講不通,乖乖拿起手榴彈到操場上去了。舊軍隊有句老話叫官打兵不羞,解放軍不打人,可是每天的罵卻也受不了,還不敢還嘴,否則就犯了“不服從”的天條,城市兵到部隊最受不了的就是這個。寧願挨打不挨駡,打上幾軍棍不叫喚還挺英雄的。
為了少挨班長的罵,我拼命苦練各種軍事技術,練投彈把胳膊練腫了,吃飯拿不住筷子,哆哆嗦嗦怎麼也扒不到嘴裡,眼看大家都吃完了,自己的飯盆還滿著,急得眼淚噗噗嗒嗒往飯盆裡掉。練匍匐前進,小臂揭掉了巴掌大一塊皮,血水粘住了襯衣,晚上睡覺脫不下來,打盆溫水泡開抹點紅藥水,第二天訓練又把剛結了痂的傷口撕開了。第一次木槍對刺,我的頭盔沒戴好,頭盔和胸甲之間留了一條縫,被對手一槍刺中喉嚨,當時就倒在了地上。我覺得喉嚨好像被擠扁了,前後壁粘在了一起,不通氣,呼吸極為困難,連裡馬上把我送到了團衛生隊。在衛生隊躺了一會,軍醫給我喝了點水,嗓子通了,呼吸也正常了,醫生怕有其他問題,要送我去野戰醫院檢查,我說不用了,直接回了連隊。
這些都是每個戰士必須經歷的,我毫無怨言,只要不挨駡,什麼苦都能吃。其實我真正怕的不是訓練,而是站崗。兩個小時傻愣愣站著沒事幹閑得發慌。三連的哨位在營房東北角,很少有人去那裡,每次上哨我都帶一本書。那時能買到的只有魯迅著作單行本,什麼呐喊、彷徨、野草,三閑集、二心集、而已集,朝花夕拾、故事新編……出了有二三十種,我差不多買齊了,就是在白天站崗的時間,我讀完了這些單行本。有一天,我正在看《兩地書》,連長突然來查哨,發現我在看書,問道:“你看的啥?”
我知道違反了紀律,急忙檢討:“連長,我錯了,以後保證不在站崗時間看書。”
連長說:“我沒問你對錯,我問你看的啥書。”
我把書遞給連長,連長翻看著問:“這書寫的啥?”
“是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集。”
“許廣平是誰?”
“是魯迅的夫人。”
連長沒再說什麼,把書揣在口袋裡走了。我以為連長要抓我的典型,誰知過了兩天他把書還回來了,又拿走了我的筆記本。
週四下午政治學習,我被抽出來辦黑板報,學習散場之後,副班長跑來問我:“《共產黨宣言》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1848年。你問這個幹嘛?”
“指導員說是一千多年前發表的,我覺得有點不對,所以來問問你。你說得准嗎?”
那時我還年輕,忍不住想出風頭,吹了個大牛:“當然准啦,《共產黨宣言》我背都能背下來,日子還能記錯?我床頭就放著一本呢,不信你去查。”
這話很快就傳到了指導員耳朵裡,第二天他來找我,讓我給全連講《共產黨宣言》。沒想到吹牛吹出這樣的結果,這可難為我了。我說講不了,指導員說,背都背下來了怎麼講不了!我只好硬著頭皮上陣。
如果當時能找到一點背景資料,這個課我能拿下來,可是我手裡只有一本原著,什麼參考資料都沒有。我不能犯指導員那樣的錯誤,只好圍繞原著做文章,好在能背誦一些段落,這些背誦可以打發掉一些時間,其餘時間就花在解釋原文上,這樣不管講好講壞,都不至於鬧笑話。我講了一個小時,不知道講得對不對,估計下面聽的人也不知道,但是那些背誦很唬人,把一個連的人都鎮住了,從此大家對我刮目相看,班長再也不罵我了。
二
我終於獲得了大家的認可。那年10月,我被評為師一級學毛著積極分子,相當於二等功,全營只評了我和副營長兩個人。其實入伍以後我就沒學過毛著,如果評學魯迅積極分子,我當之無愧。
副營長帶著我到師裡參加經驗交流會,混著吃了一周大盤子,每頓八菜一湯,早晨是四樣小菜,鹹鴨蛋、醬豆腐、糖蒜、鹹菜絲,牛奶豆漿包子油條隨便吃。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營養補充,別說那八菜一湯,就是早餐的鹹鴨蛋醬豆腐也是難得的奢侈品。開始時大家都很斯文,不好意思放開吃,副營長說,都吃光!剩下了炊事員會以為做多了,下次立刻減量,吃光了他們以為不夠,還會多添。果然,第二天每個盤子裡的菜量都加大了。我們這一桌都是基層連隊來的,肚子裡沒油水,有多少吃多少。就這樣,頓頓吃光,不斷加量,哪一桌都沒有我們這一桌菜量大。吃到後來真的吃不了了,感覺像是犯罪。
回到連裡,我被調到連部當文書。文書兼軍械員還管著全連戰士的檔案。我沒想到會在這裡看到自己的檔案。中學畢業的思想品德鑒定是工宣隊一位師傅寫的,因為我們喜歡老師的課不喜歡他的,因而懷恨在心,給我的評語幾乎沒有一句是正面的,其中有該同學一貫驕傲自滿,不尊重老師和工宣隊師傅,不服從組織領導,自以為是,誇誇其談,做事不負責任,喜歡自作主張,思想意識中充滿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骯髒情調,需要徹底改造云云……氣得我火冒三丈,幸虧四公司給我的鑒定還不錯,否則我當不了兵。
到了連部不參加訓練,每天有大量時間看書,可惜找不到書,那些魯迅單行本早已翻得滾瓜爛熟。鎮上有個新華書店,我經常去那裡,看看有沒有魯迅的新書,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了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當時只出了四卷,我全部買了回來,後來又買到幾本《中國通史資料簡編》,可惜一套書不全,只有三冊還前後不搭界。我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只要是書就買。連裡有幾個城市兵,經常能搞到書,來自南京的一位戰友家裡訂到了《學習與批判》(文革後期比較有影響的雜誌),按時給他寄,每一期來了我都要從頭讀到尾,一字不落。後來又有了一些供領導幹部看的內部書流傳,如《基辛格回憶錄》《領袖們》《回憶與思考》等,不過那種書很難借到,借書的人排長隊,拿到手後第二天就要還,白天沒時間,夜裡熬一個通宵也要看完,好在我掌管著軍械庫,不用借助手電筒或蠟燭。有一天借到一本喻守真的《唐詩三百首詳析》,如獲至寶,花了幾個晚上把詩全部抄了下來。
連長指導員都知道我愛看書,對於我在工作時間看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從來沒有批評過。連裡其他幹部對我也另眼相看,經常來找我討教一些問題。一種飄飄然的感覺開始在我身上蔓延。
第二年,連隊被抽調到蘭州軍區配合體育館工程施工。第一個任務是挖地基,土方量相當大,沒有任何機械配合,全靠洋鎬鐵鍬。一個連不夠,又從警衛營臨時抽調了一個連。兩個連展開競賽,剛開始平均每人只能挖5方,到後來竟然達到20方,大冬天的光著膀子都是滿身大汗,早晨天不亮就進入工地,晚上頂著月亮回來,每天工作量達12個小時,三頓飯都在工地上吃,有的戰士累得實在受不了了,收工後坐在地上哇哇大哭。
地基挖好之後,甘肅省建二公司進駐了工地,戰士們改為當小工,體力上輕鬆了許多。體育館的預算十分緊張,為了省錢,各種安全措施都不到位,工作環境非常危險。最危險的是高空作業,主體框架起來之後,戰士們要爬到二十幾米高的屋頂框架上幹活,框架是網狀結構,連接網結的是不到20公分寬的槽鋼,戰士們抱著幾米長的跳板、扛著幾十公斤重的焊條在槽鋼上走來走去,下面連防護網都沒有,掉下去必死無疑。現在想起來依然膽戰心驚。
我當文書,每月底要回團裡報一次實力。所謂報實力就是報一下人員傷亡增減數位,一張表格填不了幾行。這個數位是機密,不得用電話電報郵件傳遞,必須派專人送達。為此還給我配了一個帶鎖的牛皮檔包,那是個招賊的東西,我不敢用。
團裡有不少幹部在蘭州有親屬,知道我每月往來一次,經常讓我給他們帶東西,油米麵豬肉大蔥什麼都帶,有一次居然帶了六個提包外加50斤大米,我說帶不了這麼多,留守班長說:“都是首長,你能拒絕哪一個?怎麼都得想辦法帶回去,否則連長指導員都不好交代。走,我送你上火車。”
這邊有人送,那邊卻沒人接,下了車,六個包,我一手提兩個,左肩挎兩個,右肩還扛著一袋大米,雙肩都有東西,肩膀不能偏,只好直著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挪,心想,真拿戰士不當人!
月臺上有小紅帽,可以用小推車幫我把東西送出去,一件五毛錢,我覺得太貴不值得,一個人把東西扛到了出站口,結果嚴重超重,按公斤數罰款,罰了五塊多。
三
那年八月,指導員通知我去體檢,準備提幹。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是我奮鬥的起點目標,只是沒想到來得這麼快。按規定,服役滿兩年才能提幹,我只有一年八個月的軍齡,難道是破格提拔?
體檢之後便沒了消息。過了幾天,一位軍首長來連隊視察,這是連隊少有的殊榮,天大的面子,連長指導員想請首長給戰士們講講話,首長說太忙,沒空,只和連長指導員單獨談了一會就走了。
又過了幾天,從野戰醫院調來一個人,接替文書工作,我下到班裡當班長。可是他的任命宣佈了,我的卻沒有,連長讓我先在連部待著,等全連骨幹(特指班長、副班長)調整完了再下去。
新來的文書叫張保爾,長得十分瘦小,個子不足一米六五,體重不到50公斤,風一吹就倒的樣子。我要給他交工作,他不肯接,說等我臨走的時候再交接。
連部有通訊員、司號員、衛生員、理髮員,文書是班長,一下冒出來兩個班長,幾個戰士不知有事該請示誰,我說當然是現任文書,張保爾則堅持聽老文書的。局面很尷尬,我請示連長,連長說他不接你就先幹著。
張保爾來到連隊沒幾天,大家就把他的底細摸透了,原來他就是前幾天來過的那位軍首長的兒子,在野戰醫院當衛生員,他十五歲參軍,和我一樣大,已經五年軍齡了,幾次提幹都沒提起來,因為醫院有規定,業務幹部必須有專業學歷背景,軍政後勤幹部必須有連隊生活經歷。張保爾這兩條都不具備,只好到戰鬥部隊來解決。大家都說他是來頂替我提幹的。
這些閒話又給我和張保爾之間增加了一層尷尬。當然,更尷尬的是他。只要我一出現,他的目光就一直跟著我,我要幹什麼,他立刻放下手中的事來幫忙。有時他正坐著,我一進門他立刻就站起來,惶恐不安地搓著兩隻手,仿佛見到了大首長。不過這種尷尬局面很快就打破了。
張保爾帶來不少書,他還有借書的管道,我想看什麼書,他幾乎都能找到。他也愛看書,看的書比我多多了,有些世界名著我聽都沒聽說過。有一次他問我,有內部版的《紅樓夢》你要不要?我當然要啊!過了沒幾天,他就托人給我帶來一套四卷本的《紅樓夢》,印刷裝幀在當時都是一流的,漂亮極了,封底印有“內部交流,禁止出售”八個小字,是給高級幹部看的,四塊錢一套。我給他錢他不要,我硬把錢塞給了他。
在書上我們找到了交流的話題,總算度過了那段尷尬的時光,沒有發生任何矛盾衝突。到了來年一月,團裡的任命下來了,當然是他不是我。任命沒有在連裡宣佈,任命的什麼職務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提了。任命剛下來不到一周他就調走了,從來到走,剛好三個月,走時連招呼也沒和我打。
四
當兵兩年,我的身體比過去結實了不少,各項軍事技術也還過得去,我的長項是射擊,每次都是優秀,從未打過良好,但是體能依然很差。當文書期間表現不明顯,回到班裡就暴露出來了,重體力勞動和訓練仍然吃不消。體能差也要和別人幹一樣的活,一樣參加重體力訓練,吃的苦比別人格外多。因為我能吃苦,不叫苦,那年七月,連裡給我記了三
1975年下半年,體育館工程進入尾聲,我們隨大部隊移防到天水。年底之前,連裡又讓我去體檢,這一次還是沒有批。上一次是空降兵,這一次是地下黨,團裡一個幹部的侄子在我們連當班長,後來居上排到了我前面,營黨委討論的時候,認為他不成熟,沒有批,白白浪費了一個提幹指標。
我要求復員,連長指導員苦苦挽留,說你的事我們一直在努力,不要辜負了組織上的希望。我知道他們是真心對我好,但是提幹的事情他們做不了主,兩次被頂替他們都為我說過不少好話,無奈上面的意圖頂不住,所以我還是要走,最終他們也沒同意,強行把我留下了。
天水的營房是1969年修建的,當時中蘇關係正緊張,部隊住在甘泉鎮附近的幾條山溝裡,一個營一條溝。上級要求利用山區特點挖窯洞,防止敵機轟炸,可是甘泉附近的山坡度小,挖不了窯洞。部隊住在山溝裡本身就很隱蔽,敵機來了隨處可以躲藏,挖不了窯洞可以不挖,但是沒有人敢把這個意見反映給上級,上級的意見就是命令,讓修就得修,於是就想了個蠢得不能再蠢的辦法,在山坡前的平地上箍窯,窯頂再蓋上一米多厚的土。可能是土裡混進了葵花籽,經過風吹鳥啄葵花籽逐年散開,我們到來的時候,滿房頂長滿了向日葵,真是一道奇異的風景。
部隊回到天水,指導員調到集訓隊去了。新來的指導員田青雲是剛畢業的工農兵學員,來自陝西農村,走之前是個排長,回來之後破格提升,成了團裡重點培養的幹部。田指導員很能說,政治學習一講就是四五個小時,恨不能把他剛學到的那點知識一下子全部倒給大家,經常搞得推遲開飯。週一晚上的黨團活動時間也延長了,田指導員認為過去的黨團活動完全是走形式,做樣子,每次黨團活動都給大家佈置一大堆學習材料,先念後討論,他挨個黨團小組去聽,哪個組先散了就要挨批評,搞得誰也不敢先散,直到到熄燈號響才結束。
每天開始訓練之前,連長都要集合隊伍講一講當天的訓練內容、要求和注意事項,三五分鐘結束。連長講完田指導員還要講,一講就是半個多小時。有一次他講了一個小時還沒結束,連長實在看不下去了,打斷他說:“指導員,剩下的內容留到週四下午再講好不好?”這一下駁了他的面子,週四下午學習,連長沒來,田指導員對通訊員說,去叫連長來參加政治學習。通訊員跑了一趟回來報告說連長有事來不了,田指導員說,再去叫,讓他先把手裡的事放下,什麼事比政治學習還重要?通訊員又叫了一次,回來說連長忙完了就來。指導員說,那咱們就等。大家坐在飯廳裡一直等到開飯連長也沒來。
全連上下對田指導員這種霸道作風都看不貫,矛盾一爆發,幾乎一邊倒地站在連長一邊。田青雲感到了恐慌,挨個找班排長談話,有一天下午輪到了我。
“聽說你是個秀才,提了幾次都沒提起來,太委屈你了,回頭我給上邊說說,今年無論如何也要把你的問題解決了。”
“指導員就別費心了,說也不起作用,我已經做好年底復員的準備了。”
“你放心,咱上邊有人,就是一句話的事。”
對這種赤裸裸的封官許願的作法我很反感,但是也不得不應付:“那我就先謝謝您了。”
“幹事情嘛,手底下得有一把子人,上邊得搭上線,以後跟著我幹,你的前途包在我身上了。”
這明顯是在拉幫結派。過去連裡幹部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從來沒有人拉幫結派,也沒聽到過任何一個領導這樣說話,感覺像是吞了一隻蒼蠅。我以為他這種做法起不了什麼作用,誰知還真有人跟著跑。開始只是一兩個,後來越來越多,全連的班排長分成了兩派。不久,連裡傳出連長要轉業的消息,原來擁護他的那些人立刻轉向了指導員一邊,唯恐落在別人後面。
連長是1958年的兵。按規定,軍齡滿15年的副營職以上幹部可以帶家屬,並解決城鎮戶口,這對基層幹部的生活來說是一步登天的變化。連長軍齡早就夠了,身體還不錯,再提一級完全有可能,這下栽在了田青雲手裡,過了沒多久果真轉業了。
俗話說,言多必有失,田青雲講課時也會像老指導員那樣犯一些常識性錯誤。有一次他講到宋慶齡和魯迅的友誼,說兩人克服重重困難,給八路軍、新四軍搞藥品,直到抗戰勝利……我忍不住糾正了一下,“指導員,魯迅1936年就死了。”
我忘了他是誰,他哪有老指導員那樣的胸懷,加之我一直沒有表態站隊,以為我故意出他的醜,從此公開對我進行報復,整天找七班的毛病,動不動就在全連大會上點我的名,處處羞辱我,我忍無可忍,在一次全連大會上和他頂了起來,誰知他早有準備,不緊不慢地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紙說:“難道我說你說錯了嗎?你自己是個什麼人你不知道嗎?你看看這上面寫的什麼?”
說完,他打開那張紙一字一板地念道:“該同志一貫驕傲自滿,不尊重老師和工宣隊師傅,不服從組織領導,自以為是,誇誇其談,做事不負責任,喜歡自作主張,思想意識中充滿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骯髒情調,需要徹底改造……”念完,他得意洋洋地問我:“這是你檔案材料上寫的,白紙黑字,我沒冤枉你吧?”
我說:“還有一份鑒定呢?你怎麼不敢拿出來念?”
田青雲只當了半年指導員就調走了,這半年他把連隊搞得烏煙瘴氣,雞飛狗跳,把人性中最卑劣醜陋的一面全部調動了出來,連裡打小報告成風,到處都是他的密探,我在班裡的一舉一動他都知道,夜裡說句夢話都有人報告,我手下八個兵,不知道哪一個可以信任。他不光對我一個人如此,凡是他眼裡的反對派都是同等待遇,甚至對那些跟他跑的班排長,身邊也要安排臥底,以掌握他們的動向。
田青雲調走是因為碰到了更厲害的對手。新來的連長是軍幹子弟,父親是個師級幹部,才來了一個月兩個人就鬧翻了,連長要求上級把田青雲調走,否則他就走,有他沒我有我沒他。於是田青雲被調到機關當了宣傳幹事。
五
天水處於隴南原始森林的邊緣,連隊駐地風景絕佳,背靠山坡,前臨小溪,對面山上鬱鬱蔥蔥,開滿了紅的黃的白的各種野花。夜間站哨,真是一幅“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美麗圖畫。可惜那時整天忙忙碌碌,沒有好好欣賞。副連長看中了這裡大片的荒地,號召大家種菜,各班展開競賽。我對種菜很感興趣,下了不少工夫,每棵西葫蘆下面要挖一尺多深的坑,農村戰士告訴我用不著那樣,我聽不進去,照樣幹,後來果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一個夏秋給炊事班交了1700多斤菜,全連第一。
副連長一個人單獨開闢戰場,拿個䦆頭在山坡上種玉米,也不翻地,刨個坑撒幾粒種子就算完事,出苗以後蹭蹭地長,收穫的時候全連天天吃煮玉米棒子,香極了。
入伍第四年,我被選為連隊革命軍人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副連長,我是唯一副主任。我極力推辭,因為我還擔任著團支部副書記,也是唯一的副書記,同時還兼著黨支部委員。戰士委員只有兩個。我把三個組織的戰士位置都占了,別人還怎麼進步!副連長說,這是大家選的,連裡也沒辦法。
軍人委員會類似工會,主要職能是維護軍人的個人權益,特別是戰士的權益。過去軍人委員會一直是作為擺設放在那裡,偶爾提一些改善伙食之類的不疼不癢的意見,從來沒有人敢站出來真正維護戰士的權益。既然大家選我,我就不能辜負大家的信任。我把各種侵犯戰士權益的問題梳理了一下,提出了七條改進意見:
- 切實貫徹官兵平等原則,尊重戰士人格,不得隨意辱駡士兵;
- 尊重戰士的個人權利,不得隨意拆看戰士家信;
- 科學訓練,除緊急情況外,不得在飯後半小時內要求士兵進行訓練或重體力勞動;
- 幹部家屬來隊,須按規定繳納伙食費和糧票,不得隨意從炊事班拿東西;
- 不得將連隊生產的蔬菜、豬肉以及糧油米麵等物品隨意送給上級領導;
- 不得以招待客人為名開小灶大吃大喝;
- 司務長須每月公開帳目,交革命軍人委員會審查,供全體官兵監督。
這些意見在連裡引起了巨大反響,所有的人都在議論。士兵們當然贊同,幹部們卻有些狼狽,因為這些意見主要是針對他們的。一些幹部開始對我敬而遠之。
開完會,副連長把我叫到他房間。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多才多藝,寫得一手好文章,能作詩作詞,自己還創作軍旅歌曲,軍事技術出類拔萃,曾在師教導隊當過教官,在周圍的幹部中鶴立雞群,就是不肯巴結領導,遇到不合理的事就想說,因此一直提不上去。他本是個當將軍的料,卻在副連長位置上窩了整整10年,直到轉業。
副連長,我的入黨介紹人
聽了我在會上的發言他很擔心,一進門便說:“你捅了馬蜂窩了知道不知道?”
“知道,我就是想捅捅這個馬蜂窩。”
“你不想在這混啦?”
“我確實不想在這混了,即使在這混,該捅還得捅,否則大家選你幹嘛?”
“你怎麼一根筋哪?你也不想想,這些年連裡幹部對你都不錯,你多少也得給他們留點面子吧?萬一你今年提了幹,怎麼和他們相處?”
“這個我沒多想,不過我的意見並沒有針對哪一個人,只是一些原則。”
“可是這些原則都是針對他們的。我真替你擔心哪,已經熬了四年好不容易快熬出頭了,自己把自己的前程給斷送了!”
七條意見本來是要提交連黨支部討論形成決議的,副連長壓著沒交,革命軍人委員會也沒再開過會,但是那些意見卻起到了實際作用。那時候人們還知羞恥,短時間內吃、請、送、拿的現象基本杜絕,至少不敢公開這樣做,但是尊重士兵的人格、權利仍做不到。三五槍三五彈照樣搞,對士兵該罵照樣罵。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家信,發現信被拆過了。我的信被拆不是一次兩次了,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當著全班的面發作起來:“這是誰幹的?私拆別人信件是違法的知不知道?”
信是八班副趙小小帶給我的,見我沖他發火,轉身就走了。他前腳走,連長後腳到:“你在這喊什麼呢?”
部隊裡連長指導員看戰士家信是天經地義的事,代表了組織上對戰士的關懷,從來沒有人提出過異議,我這麼憤怒連長感到莫名其妙,覺得我是無理取鬧,把組織上的好心當成驢肝肺,劈頭蓋臉把我訓了一頓,我覺得他太無知,兩個人大吵了一通。
趙小小是從七班出去的,當了副班長之後,對我依然恭恭敬敬,總是叫我班長而不是七班長,以表示他還是我的兵。
我的兵出門就把我賣了,連長年輕沉不住氣,轉身又把他賣了。晚上,趙小小來找我解釋,我說:“告就告了吧,敢作敢當,還解釋什麼!”
趙小小賴不過,只好承認:“是我告訴連長的,但是我絕沒有害你的意思,是你一手把我帶出來的,這輩子我永遠都是你的兵,我怎麼能……”
我打斷他說:“我沒你這號兵!”
“你聽我說班長,我真的是從內心裡尊重你,一直把你當成兄長,當成拐棍……”
我不知他是怎樣一種思維方式,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來,也許是真情流露?我聽了很意外,也很吃驚:“現在拐棍用完了該扔了是不是?”
“那什麼班長,我說錯了,你聽我解釋……”
我怒不可遏,沖他吼道:“你給我滾出去!”
六
天水的營房蓋了還不到10年就沒法住了,一是房頂土質鬆軟吸水排不出去,窯洞裡潮得像水簾洞,一串串水珠順著牆壁往下淌,二是窯頂壓力不平衡造成下面牆壁出現了裂縫,成了危房,上級決定拆除蓋新營房。全營各連隊先後撤出溝外,每個連留一個班拆除舊窯洞,溝裡只剩了我們連暫時沒搬。隔壁一連幾個拆房的戰士取巧,不從頂上開始從下面掏,掏得差不多了窯頂會自己塌下來。五個戰士在裡面掏,一個在外面觀察,看窯頂快塌的時候喊一聲,大家趕緊往外跑,連拆了四間都沒事,到第五間的時候沒跑出來,五個戰士全部被砸死在裡面。
聞聽出事,全連官兵立刻撲上去拼命地往外挖,挖出來的時候一個個全身的骨頭都砸碎了,一抬是軟的,慘不忍賭,沒人敢上前收拾,我是兵頭兒,只好硬著頭皮上,扛出了第一具屍體,眾人把他放在我肩上的時候,只聽得頭骨嘩啦嘩啦響。
出事之前司務長花五塊錢買了一頭驢,中午要給大家改善一下,沒想到出了這事,誰也吃不下,全倒了。我因此一輩子不吃驢肉。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到了年底,連裡又讓我去參加提幹體檢,這一次依然沒有批。我以為自己不過是個陪綁的,其實還真不是。復員之前,連長找我談了一次話,說明了原委:“你知道我為什麼找你嗎?我就是要告訴你,是我力主把你拉下來的。”
“為什麼?就為那次吵架?”
“對,我剛來沒幾天你就跟我過不去,讓我怎麼開展工作?我咽不下這口氣!咱明人不做暗事,是怎麼回事就怎麼回事,你可以恨我,罵我,我也不躲不藏,是我幹的就是我幹的。”
“幹得漂亮,謝謝你!”說完,我轉身走了。
復員之前,後勤部門把我們穿了四年的羊皮大衣收走了,換了一件棉大衣。那大衣實在是太舊了,還是戰爭年代的產品,雖然拆洗過,有些衣服上仍然帶著血污的痕跡,土黃色,布面都糟了,一碰就是一道口子。此事引起了老兵的強烈不滿,聯名寫信提意見,後勤部門解釋說大衣和褥子屬於營房配備物品,年年都是這麼處理的,不可改變。
連隊從山裡撤出後暫時住在老鄉家。一大早,新班長帶著大家到新營房工地上去了,我因等待復員不必出工,一個人待在屋裡看書,忽聽趙小小在院子裡喊:“班長,指導員送你來了。”
話音剛落,趙小小領著田青雲進來了。我真的以為他是來送我的,戰友們平時有些恩恩怨怨,到了分手的時候一般都釋懷了,沒想到他是專程來羞辱我的,一坐下便連諷刺帶挖苦:“……你看,當初我讓你跟著我幹你不聽,現在怎麼樣?四年白乾了吧?早知如此你何苦呢,在廠裡老老實實當個工人多好!你說你這四年損失有多大!我給你算了一筆賬,至少損失兩千塊錢的工資,不過我知道你覺悟高,可以為國家無私奉獻,好同志!好同志呀,值得我們學習……”
我覺得我們之間並無深仇大恨,即使有他也報得差不多了,在連裡一直是他整我,我幾乎沒有還手之力,想不到他居然這樣狹隘,這樣下作,我不屑於和他鬥口舌,一句話也沒說,等他說完我說:“說完了麼?說完你可以走了。”
“急啥嘛,我們畢竟在一起共事半年多,老戰友了嘛,多聊會兒……”
他一邊說一邊拿起床上的大衣:“……這大衣不錯嘛,可惜就是舊了點。”說著,他故意把大衣撕了一道口子,“呦!布面這麼糟!對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回去你再縫縫吧。這是什麼年代的大衣呀,是日本鬼子穿的吧?”
說完,他把大衣穿在了身上,“你就穿這個回家?那不跟鬼子進村一樣嗎?”我終於忍無可忍,從槍架上抓起一支步槍,刷地一下打開了刺刀。一見這陣勢,兩個人撒腿就跑,連大衣都沒顧上脫。是房東把大衣送回來的。
1977年3月,我離開了灑下四年汗水的連隊,回到原單位四冶四公司。在家待了一個多月沒去報到,損失一個月的工資也不在乎,我想靜下心來好好總結一下。開始時覺得自己很失敗,走時是個兵,回來還是個兵!後來慢慢就想通了,作為一個戰士,我做了所有我應該做的,也獲得了一個戰士所能獲得的所有榮譽,我努力了,也得到了戰友們的認可,提幹提不起來有我個人性格的原因,也有環境的因素,我的性格遇到這種環境發生衝突是必然的,結局早已註定,而讓我改變自己屈從於環境是不可能的。當兵四年,雖說是一場不成功的奮鬥,也並沒有失敗。我是一個優秀的戰士,我應當為自己感到自豪。新的生活正迎面向我走來,我依然信心滿懷。
不久,我收到一封戰友來信,信中說田青雲被隔離審查了。大約是在1976年9月,他糾集了幾個軍官給江青寫了一封勸進信,還上躥下跳地動員各級指揮員簽名,捲進了政治鬥爭。事情鬧得很大,最後怎麼處理的不得而知。
九個月之後,我考進了蘭州大學。
2020年9月24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