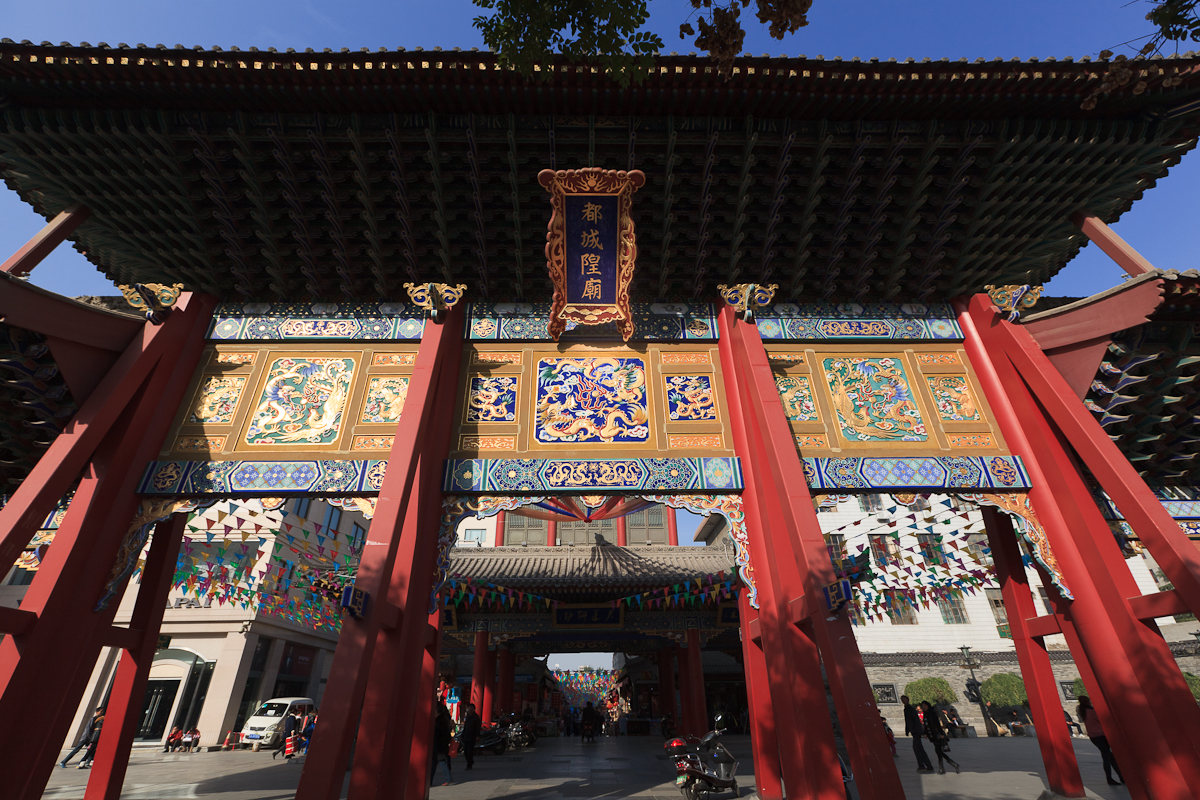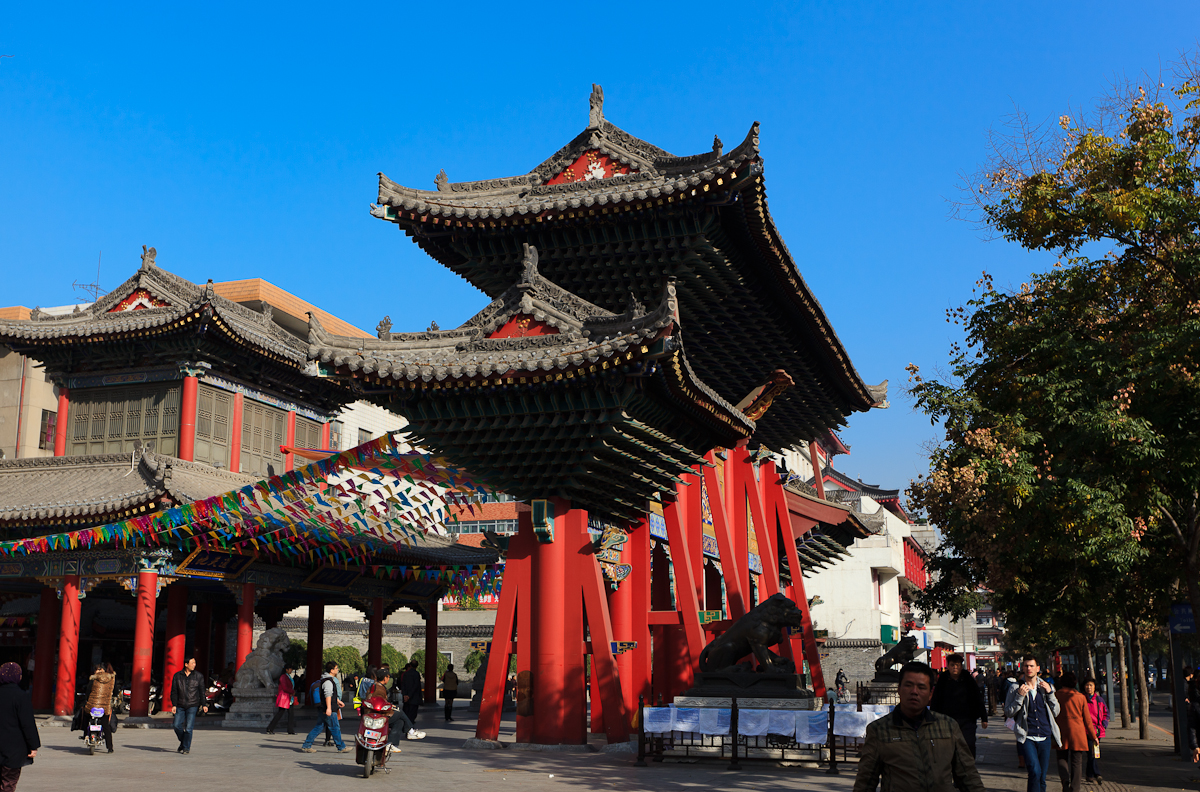那一梭子彈穿透了我的胸膛
於澤俊 2021/12/02刊
三娃是我入伍後第一個認識的戰友,我們是坐同一輛悶罐子車來到部隊的。那是1972年的冬天,車外天寒地凍,雪花飄飄,尖利的北風無孔不入,從車廂的各個角落裡鑽進來,凍得人手腳冰涼。新兵到部隊以後才發大衣,棉軍裝抵禦不住車裡的寒冷,只好用被子裹住下半身,坐在破舊的稻草墊子上,仨一群倆一夥地瑟縮在一起相互取暖。車上每隔一米左右有一個一尺見方的小窗戶,有抽拉門,可以打開,內急的問題就在這裡解決,要辦大事得等到了兵站再說。白天車廂裡並不是太暗,借著視窗和四面縫隙裡透進來的光線可以看書。
我拿了一本《魯迅雜文書信選》坐在視窗,剛打開,睡在我旁邊的三娃湊過來問:“你看的啥?”
我把書合起來給他看封面,他茫然地望著我,說:“俄不識字。”
我說這是魯迅的書,他仍是一臉茫然。我只好放下書,和他聊別的:“你是哪個公社的?叫什麼名字?”
“俄是三十里鋪的,叫探三娃。”
“探三娃,哪個探字?”
他抓過我的手,在我手心裡寫了一個“淡”字。
我說:“這個字念淡,不念探。”
“俄們那裡都念探。”
“你們那的念法是錯的。淡,淡三娃。”
“蛋?難聽得很!”
三娃一口隴西話,說什麼也不肯把姓由“探”改成“淡”,我說服不了他,只好接著看我的書,三娃拿出一塊上車前發的點心,禮貌性地讓了讓:“你吃!”
“你吃吧,不是都有嗎?”
三娃用雙手恭恭敬敬地捧著點心咯吱咯吱吃了起來,這是西北農民吃饃的標準姿勢,神態極其莊重,那種莊重代表著他們對糧食的崇敬。
看見他吃的那麼香,我也覺得餓了,拿出一塊吃了起來。因為等車來不及吃午飯,每人發了十塊點心,用紙包成一個直筒。點心是隴西食品廠生產的,類似月餅,裡面青絲玫瑰冰糖各種配料一樣不少,就是工藝太差,梆梆硬,咬不動,因為積壓得太久,一股油哈喇味,難吃極了。我吃了兩口就撂下了:“難吃死了!”
三娃一愣:“你說啥?這麼好的點心你說難吃?”
“你覺得好吃嗎?”
“當然好吃,俄們那搭哪見過這東西!一年到頭吃的是洋芋,有時連洋芋都吃不上。”
我拿起點心筒遞給他說:“你覺得好吃就送給你吧,我是吃不下這東西。”
三娃瞪大眼睛望著我說:“你真格不吃?”
“不吃。”
三娃接過點心,小心翼翼地放進了挎包裡,然後問我,“聽說你是從廠裡來的,你為啥要當兵呢?”
我不想說理想、追求一類的大話,一時又找不出合適的答案,於是反問道:“你呢?”
“俄想掙些錢,回來娶個媳婦。”
“掙錢娶媳婦?當兵能掙什麼錢!一個月六塊錢津貼,不夠買兩條煙的。”
“第一年六塊,第二年就七塊了,第三年八塊呢!72加84再加96,三年下來就能掙252塊錢。要是能當上四年兵,俄就發大財了!”
三娃不識字,小帳來得倒挺快。
“那你當兵三年就一分錢不花?”
“吃的穿的國家都管著呢,哪有咱花錢的地方?”
“你不刷牙洗臉哪?肥皂、牙膏也不買?”
“俄這樣的臉還用肥皂?把肥皂糟蹋了!”
說到臉,我不由自主地朝他臉上看了一眼,心裡直發麻,他那臉蛋紫裡透黑,跟茄子一樣顏色,上車之前我一直躲著他,害怕看到他這張臉,誰知上了車,排長竟然把我倆的鋪位分到了一起。隴西一帶的水土不知缺什麼元素,孩子們大多是紅臉蛋,很多山裡的孩子就像三娃這樣,臉紅得發紫發黑,好像得了嚴重的皮膚病。
“就算你一分錢不花,兩百五娶個媳婦也不夠啊!我聽說娶個媳婦少不得300元。”
“那是川裡人,俄們山裡便宜,兩百元就夠了,兩百五十元那就隨便挑了!”說到這,三娃的眼睛都亮了。
我笑著說:“那好啊,等你娶媳婦的時候到你家去喝喜酒。”
“你娶了麼?”
“沒有。”
“說哈(下)了沒有?”
“沒有。”
那你為啥要去當兵呢?”
這話我還是沒法回答,只好用隴西話跟他調侃:“俄就想當個兵。”
三娃又問我工資是多少,聽我說學徒期滿每月可以掙48塊錢,三娃驚訝得倒吸了一口氣,驚呼道:“噫——!你個瓜娃娃,你虧死了!”
他這一喊,把全車廂人的目光都吸引了過來。
火車走走停停,從隴西到蘭州,只有200公里,走了八九個小時,半夜12點才到蘭州兵站。我已經餓得挨不住了,對三娃說:“把那點心給我一塊。”
三娃不好意思地答道:“俄吃完了。”
“什麼?20塊點心你都吃完了?!”
兵站的伙食不錯,院子裡擺著十幾個裝滿米飯的大木桶,每個木桶旁邊是一大盆豬肉白菜燉粉條。飯是足夠吃的,可是這些新兵一進兵站就亂了套,一個個手舉著剛發的刷牙缸子,上去就搶,每個飯桶跟前圍得裡三層外三層,後面的搶不到,爬到了前面的頭頂上,前面搶到的被壓在下麵出不來,不一會兒就把地上的菜盆子全踩翻了,活像一群耗子,看得我目瞪口呆。帶兵的幹部怎麼喊也彈壓不住,只好拳打腳踢往下拉,拉下來一個揍兩拳,一鬆手又衝上去了。最後只好放手不管了。
三娃拉著我要往上衝,我說:“這飯我不吃了。”
三娃不由分說,一個助跑衝了上去,爬到了人群頂上,不一會,他端著半缸子白米飯過來了,看見我還站在原地沒動,把米飯往我手裡一塞,拿著我的空缸子又衝了上去。
帶隊的幹部怕出事,急中生智想出了一個主意:“隴西的新兵上車了!車馬上就要開了!”
這個計策果真有效,聽到喊聲,搶飯的人群立刻開始鬆動,可是還有不少人圍著飯桶不肯散去。我們這個排一多半人已經站好了隊,還不見三娃的蹤影,我到飯桶跟前去找,看見一個新兵頭朝下腳朝上紮進了飯桶裡,眾人七手八腳把他拉了上來,正是三娃,只見他滿頭滿臉都是米粒,腦袋活像個大飯團子。我和帶隊的排長拉著他往集合地點走,他還不停地回頭嚷著:“缸子!俄的刷牙缸子!”
我衝他大聲喊道:“那個缸子不要了!”
車走了兩天兩夜,第三天中午才到青銅峽,部隊就駐紮在這裡。
青銅峽位於騰格裡沙漠的邊緣,冬夏溫差很大,冬天最低氣溫零下30度,夏天則高達40多度。風沙很大,一刮起來滿天沙塵,迷得人睜不開眼睛。帶隊的幹部告訴我們:“這裡的風沙一年刮兩次,一次六個月。”這當然是誇張的說法,可是我們一下車就趕上了,狂風卷著沙粒惡狠狠地朝我們撲來,打得臉生疼,車站離營房還有十幾裡路,我們必須走過去,到了地方,鼻子耳朵裡灌滿了沙粒。
我和三娃有緣,又分到了一個連隊一個班。
連裡對新兵進行了一次體能和身體靈活度測試,我和三娃是40個新兵裡最差的,我投彈只投了23米,不及格(30米及格,40米優秀,50米為投彈能手),羞得我臉上直發燒。三娃比我還差,15米!看起來他比我強壯,可是掌握不住技巧,手榴彈脫手總是慢半拍,一出手就砸到地上了,那個寸勁想學都學不來。
部隊正在進行冬季訓練,週二和週五早操是體能訓練,週二十公里長跑,週五十公里負重行軍。每到這時候,落在最後面的總是我倆。尤其是負重行軍,一個步兵冬季裝備加起來55斤(包括身上穿的),平時訓練不背乾糧袋、水壺、子彈帶、手榴彈等東西,也得有30斤。前半段是急行軍,掙死掙活勉強還能跟上,後半段是強行軍,不管隊形,撒開了跑,這是為戰時搶佔陣地而進行的訓練。第一次強行軍,命令一下達,整個連隊轉眼間跑得無影無蹤,就剩了我和三娃。我還想努力追趕,不料背包散了,東西撒了一地,我只好停下來重新打背包,三娃也停下來幫我把掉在地上的東西一一拾起來,我一看他,忍不住大笑起來:“你把褲子穿反了!”
我和三娃回到連隊的時候,大家已經吃完早飯了,我們倆拿著飯盆往食堂走,班長黑著臉正在食堂門口等著呢:“給我站住!還有臉吃飯哪?”
我從來沒受過這樣的訓斥,紅著臉解釋道:“班長,我們不是故意拖後腿,確實是跑不動。”
“跑不動也要拼命跑!這要是在戰時,等你們趕到,仗都打完了!你看看這都幾點了?”班長指著太陽說。
“我們盡力跑了,可是我的背包散了,他把褲子穿反了。”
“小道理還多得很,打起仗來能容你們這些小道理嗎?早就拉出去槍斃了!”
寧夏幾乎沒有春天,熬過漫長的冬季,一下子就進入了夏天。營房裡的沙棗花開了,滿院子彌漫著甜膩的花香。經過半年多的訓練,我和三娃的體能和技巧都有了很大提高,我投彈能投46米,提高了一倍,離投彈能手只差四米,可是那四米怎麼也不上去,直到復員也沒能突破46米的成績。三娃的成績也達到了40米,但是不會助跑,他原地投就能投40米,加上助跑還是40米。
部隊訓練不講科學,連裡號召開展三五槍三五彈活動,吃過飯立刻就要拿著手榴彈出去投上半小時,不給一點休息時間,過了沒多久,我和三娃都得了胃病,我是潰瘍,他是胃下垂。
班長在門前樹上綁了幾根繩子,繩子的一頭綁上手榴彈,沒事就讓我們去練臂力,幾天下來胳膊就腫了,吃飯的時候拿不住筷子,哆哆嗦嗦怎麼也把飯扒不到嘴裡,眼看大家都吃完走了,我倆還沒動幾口,三娃一邊吃一邊哭,眼淚撲嗒撲嗒地往飯盆裡掉,我安慰他說:“忍著點,要不怎麼回家娶媳婦?”
最艱苦的是戰術訓練中的匍匐前進,一天下來從胳膊肘到小臂都磨破了,血水粘住了襯衣,晚上睡覺脫不下來,打半盆溫水泡開,第二天訓練又把剛結了痂的傷口重新撕開了。
我和三娃就這樣跌跌拌拌地在班長的呵斥聲中走完了一個新兵的路程。這是每一個新兵都必須經歷的,我們並無怨言,可是班長仍然瞧不上我倆,總說我訓練不刻苦,就差四米為什麼過不了五十大關!於是我更加拼命地練,還是上不去。三娃就更不用說了,每天收操點評都要挨班長一頓尅。他捨不得買肥皂牙膏,刷牙用鹽水,拿指頭抹,洗衣服不打肥皂,油垢洗不掉,和沒洗一樣。週四下午的政治學習穿襯衣,全連戰士好像較著勁比賽似的,白襯衣一個比一個洗得白,只有三娃的襯衣是灰突突的,我一再對他說,以後洗衣服就用我的肥皂洗衣粉,他總是不好意思。更離譜的是,他晚上睡覺不穿短褲,光著身子睡,天熱了夜裡蹬被子,經常赤條條躺在那裡。有一次被班長看見了,照著他的屁股狠狠給了一巴掌:“起來!把你的褲衩穿上!”
“俄沒有褲衩衩。”
“胡說!給你發的褲衩呢?”
原來入伍的時候,三娃把短褲、襯褲都留給他弟弟當外褲穿了。我到軍人服務社給他買了兩條短褲,三娃拿著那兩條短褲心疼地念叨著:這得多少錢哪!我說沒多少錢,算我送給你的。三娃不肯接受,推讓了半天,最後同意我把穿過的舊短褲給他,新的留給我自己,我說這怎麼行,他說這怎麼不行!
年底,我被調到連部當文書,同時還兼著文化教員,給幾個文盲和那些只上過一兩年學的戰士教文化課。三娃學文化很上心,我接手文化教員的時候,他已經能認七八百字了。有一天他到連部來找我,讓我給他找一些用剩下的鉛筆頭和廢舊紙張,我給他找了一些用不完的報表紙,幾支鉛筆和一支舊鋼筆,三娃如獲至寶,拿起東西要走,我說你先別走,把昨天學的生字給我寫一遍,看看你學得怎麼樣。三娃坐下一筆一畫地寫起來,他用力很猛,把紙都劃破了,寫出來的字一個個像六尺杠子搭出來的,寫完,不好意思地望著我說:“寫得不好。”我說你光會認不行,還得會寫,回去好好練!我怎麼也沒想到,第二年連裡舉行鋼筆字書法比賽,他居然得了第三名。我拿過他的作品看了看,不僅工整秀麗,還是中規中矩的柳體。我驚奇地望著他,怎麼也不敢相信這些字是眼前這個黑臉大漢寫的,“你簡直要成精了!”
那年隴西大旱,莊稼顆粒無收,三娃家裡來信讓他幫助想想辦法。那時他已經攢了54塊錢,九個月的津貼費一分錢沒動,連吃飯的飯盆都沒買,用的是復員的老兵留下來的。他來找我商量,想把這54塊錢全部寄回去,我說:“那你娶媳婦的錢就不夠了,再說,家裡主要是缺糧,你寄回去這點錢買高價糧能買幾斤?這樣吧,我來的時候還帶了一點全國糧票,我留著也沒用,你先拿去,我再問問其他戰友還有沒有,錢一分不能動。”
連裡有幾個城市兵,平時我們關係都不錯,我就把三娃的情況對他們說了。消息很快傳遍了全連,連裡有不少幹部戰士回家探親的,手裡有剩餘的糧票,大家東拼西湊,居然湊出了100多斤全國糧票。為這事,三娃還專門來感謝過我,他不會說那些客氣話,見了面只是嘿嘿、嘿嘿地傻笑。
我們團的營房挨著秦渠。秦渠不只是一條渠,而是一個覆蓋整個銀(川)吳(忠)平原的灌溉網,水是從黃河裡引的。黃河自古以來就是一條害河,到處氾濫,無法利用,只有到了青銅峽口附近,水流才變得逐漸平緩,可以把水引出來灌溉農田,因此有“天下黃河富寧夏”之說。渠是秦代修築的,故稱秦渠。為了擴大灌溉面積,充分發揮秦渠的作用,寧夏地方政府又修了一條東幹渠。到了九月底,部隊全年訓練計畫順利完成,奉命開進了東幹渠工地,支援這項工程。
各連隊之間展開了競賽。第一天,全連平均每人完成土方量五方,這是一個戰士能承受的合理勞動量,可是第二天有的連隊就創造了六方的成績,其他連隊緊趕直追,第三天又出現了七方八方的,溝越挖越深,向岸上運土越來越難,每天完成的土方量也越來越高,就這樣你追我趕,最後竟然達到了平均每人每天完成19方,還有人喊出了向20方進軍的口號。勞動量從每天的8小時,增加到了12小時甚至更多,超不過兄弟連就別想收工。早晨摸著黑走,晚上頂著月亮回來,一日三餐都在工地上吃,星期天也不休息。大冬天的,戰士們脫了衣服光著膀子幹,仍然滿身是汗,幾乎百分之九十的人得了不同程度的胃病。三娃胃下垂11公分,住進了野戰醫院。他正在爭取入黨,住了沒幾天,又被“輕傷不下火線”的宣傳鼓動給忽悠回來了。
一天晚上,月亮升起老高了連長才喊收工,幾乎所有的戰士都癱坐在地上,休息了十幾分鐘才把隊伍集合起來。三娃胃疼得站不起來,坐在地上直哭,指導員問:“怎麼回事?快去看看!”
連長、指導員和我一起來到三娃身邊。三娃本來是在低聲哭泣,一看見我們,心理一下子就崩潰了,坐在地上放聲大哭起來:“連長!指導員!這個兵俄不當了,你們讓俄復員吧!俄要回家!俄要回家呀!”
我蹲下來,趴在他耳朵邊上小聲說:“別這麼喊,這麼喊對你不好,咬牙堅持一下,多想想咱們不是還要掙錢回家娶媳婦呢麼?”
三娃根本不管那一套,扯著嗓子喊道:“這個媳婦俄不娶了!俄寧可打一輩子光棍!”
三娃再次被送進醫院。他這一鬧,把大家都救了,師部下達了命令,每天只准幹八小時,星期天必須休息,違抗命令者就地撤職!
一個月後,三娃出院了。可能是換了水土的關係,入伍一年多,隴西兵臉上的紅二團一個個都消失了。三娃的皮膚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臉上的紫黑色完全褪去,成了紅二團,像是故意化的妝;又過了些日子,紅二團也漸漸變淡,成了少男少女那種青春期的紅暈。部隊的飯把他養胖了,皮膚也變白了,看上去面若桃花,粉白粉白的,醜小鴨變成了白天鵝。
三娃的身體也不像從前那麼僵硬,靈活多了,不知從哪一天開始,他學會了投彈助跑,很快就突破了五十大關,有一天晚飯後,大家站在操場上練投彈,全連的投彈能手差不多都來了,無形中進行了一場表演賽。操場的邊界線外是一條馬路,馬路對面是圍牆。手榴彈投到操場邊剛好是50米,投到牆根是60米,那天不知是什麼神靈相助,三娃一個長距離助跑,居然把手榴彈甩到牆外去了!算上落地的弧度線,這一投將近70米!全連只有副連長一個人創造過這樣的記錄,可是那天副連長投了幾次都不成功。
那年八月,指導員通知我去體檢,準備提幹。消息立刻傳遍了全連,大家紛紛向我表示祝賀,我很尷尬。三娃也來了,在連部坐了半天沒說一句話,我說:“我知道你幹什麼來了,心意我領了,去忙你的吧。”
“俄不光是那個意思,俄還有事情問你呢……”
“什麼事?說吧。”
三娃吭哧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話:“你說俄這樣的人能提幹麼?”
我覺得可能性不大,又不願意打擊他,只好說:“能啊,怎麼不能!大家都是一樣的人,你又不比別人缺胳膊少腿!”
聽了我的話,三娃高高興興地走了。
由於一些外來因素的影響,我提幹沒提起來,下到七班當班長,三娃任副班長。我發現三娃變了,吃饅頭居然要剝皮,我當著全班的面毫不客氣地說:“你忘了在家連洋芋都吃不上的日子啦?把饅頭皮都給我撿起來吃了!”
三娃一句話也沒說,紅著臉把饅頭皮吃了。
副連長擔心糧食不夠吃,買了一萬斤洋芋。炊事班每天早晨蒸一點給大家吃,一個班半盆。早飯打回來,大家都搶著吃饅頭,誰也不吃洋芋,於是我規定先吃洋芋,吃不完洋芋不准吃饅頭。
你有政策他有對策,那洋芋大小不一,吃的時候人人都揀小的拿,用牙尖一點一點地啃,吃了半天半盆洋芋不見下,我只好強行分配。採取分配製他們也有辦法對付,有的戰士偷偷把洋芋揣在口袋裡,吃完飯再想辦法扔掉,我氣壞了,下決心要抓一個現行教育教育,沒想到抓到的竟然是三娃。那天吃完早飯,我親眼看見他把兩個洋芋扔進了垃圾桶,我站在他身後命令道:“撿起來!”
三娃乖乖地把洋芋從垃圾桶裡掏了出來,哀求道:“班長,俄把這洋芋吃了,你給俄留點面子行不行?別讓俄在全連面前丟人。”說完,他一把把一個洋芋塞進了嘴裡。
入冬前給老兵發新軍裝。我的腦袋特別大,戴62號帽子,司務長登記號碼的時候,我報的是特大號,全連只有我一個。我那頂栽絨帽是特製的,和別人的不一樣,大家都說特別漂亮,可惜我連見都沒見到。三娃去領軍裝的時候看到了,一把抓在手裡,回來就打進小包袱送進了倉庫(連隊倉庫統一保管個人的多餘物品)。我找他要帽子,他說什麼也不給,我好言好語勸說道:“我不是捨不得一頂帽子,你的那頂我戴不上,你不能讓我光著腦袋吧?”無論我怎麼說,他就是不給,我實在氣不過,去找指導員,指導員找他談了話,還是不給。為一頂帽子指導員也不能把他怎麼樣,只好回過頭來給我做工作,我說:“我不是跟他爭一頂帽子,他的帽子我戴不上!”說完,我把三娃的帽子扣在頭上讓指導員看,後面露著後腦勺,指導員使勁把帽子往下壓了壓,“這不也能戴上嘛,戴幾天撐一撐就大了。”
我哭笑不得,從此就和三娃掰了,一個宿舍裡住著,連話都不說。幾天以後,三娃收到一封家信。看完信,三娃的臉色立刻就變了,一連幾天吃不下睡不著。我知道他家裡出事了,有心問問,一想到他那樣對我,氣就不打一處來,幾次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星期天下午,我們連和一連約了一場籃球賽。打球的時候,運動員的外衣都搭在籃球架上。球打完了,一連副連長的錢包不見了。錢包裡有一張存摺,連裡立刻派通訊員到鎮上儲蓄所去掛失,儲蓄所下班了。第二天早上通訊員再去,錢已經被取走了,是頭天晚上取走的。據儲蓄所的業務員說,是一個戰士取走的,他說家裡老父親病危,馬上要坐火車回去,遲了就見不上了。儲蓄所只有兩個業務員,住的都不遠,出於同情和信任,兩個人一商量就破例把錢給他取了。通訊員回來做了彙報,連裡決定讓業務員來指認。
週二下午,兩個業務員來了。全連列隊集合,讓業務員指認。一個業務員直接走到三娃面前指著他的鼻子說:“就是他!”
隊伍解散以後,指導員把我叫到一邊說:“這事怪我考慮不周,事先沒有囑咐那兩個業務員不要當面指明,現在後悔也晚了。你回去給三娃做做工作,告訴他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把錢退了就行了,千萬不要想不開,這兩天一定要特別注意他的情緒,不能讓他一個待著,身邊時時刻刻都要有人,我擔心他會出事。”
回到班裡,我把人都打發出去了,只剩下我和三娃,我問他:“家裡出什麼事了?”
三娃把那封家信遞給了我。信是他弟弟寫來的,他弟弟腦子比他靈光,上過初中。信是這樣寫的:
哥:
咱大病了,得的是肺癌。縣醫院大夫說多虧發現得早,馬上做手術還來得及,晚了就不行了。做手術要300元,咱家哪來的錢呢?只有靠你了!哥,我知道你沒有這麼多錢,大不讓我給你寫信,怕為難你,可是咱不能看著大這樣不管哪!現在只有靠你了,你想想辦法,跟人借一些,將來我和你一起還。哥,我心裡急得很,你一定要想辦法救救咱大,儘快把錢寄來,晚了你就見不上咱大了……
看到這裡,我的眼睛潮濕了,“你怎麼不早告訴我?我可以幫你想辦法呀!”
“俄沒臉找你。俄這一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你。”
“說什麼呢?你怎麼對不起我了?不就一頂帽子麼!”
“明天俄就把帽子還給你。唉,做哈這樣見不得人的事,虧先人哩……”
說罷,三娃抱頭痛哭。
第二天出早操,三娃不想去,說沒臉見人,我說不去就不去吧。早操時間每個班留一個值日生,負責打開水搞衛生,我把值日生叫到門外囑咐說:“今早開水不要打了,搞搞衛生就行了。”說完,我衝屋裡努了努嘴,值日生表示明白。誰知早操隊伍剛跑了兩圈,就聽見一陣沉悶的槍聲,我心說不好,出事了!撒腿就往回跑。
回到宿舍一看,果真出事了。三娃光著腳躺在地上,身邊滿地是血,旁邊扔著一支自動步槍。他是用胸口頂著槍口,用腳拇趾扣動的扳機,一梭子子彈全部射進了胸膛。望著血泊中的三娃,我悲痛欲絕,仿佛那子彈同時也射穿了我的胸膛……
部隊裡很多老兵手裡都有子彈,有的是在實彈射擊時偷著在子彈箱裡抓的,有的是校槍時留下的,也有的是找能管事的熟人要的,為的是復員回去當民兵時顯擺。不知三娃是怎麼搞到的。
這時,值日生提著幾個暖瓶回來了,我上去揪住他的衣領吼道:“誰讓你去打水的?我不是告訴你不要去嗎?”
“是副班長讓我去的,他說他沒事,我看他正幫我打掃衛生,情緒挺好的,不像有事的樣子,就……”
我鬆開值日生,轉過身,忽然看見那頂軍帽端端正正放在我床頭的被子上,頓時淚如雨下……
202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