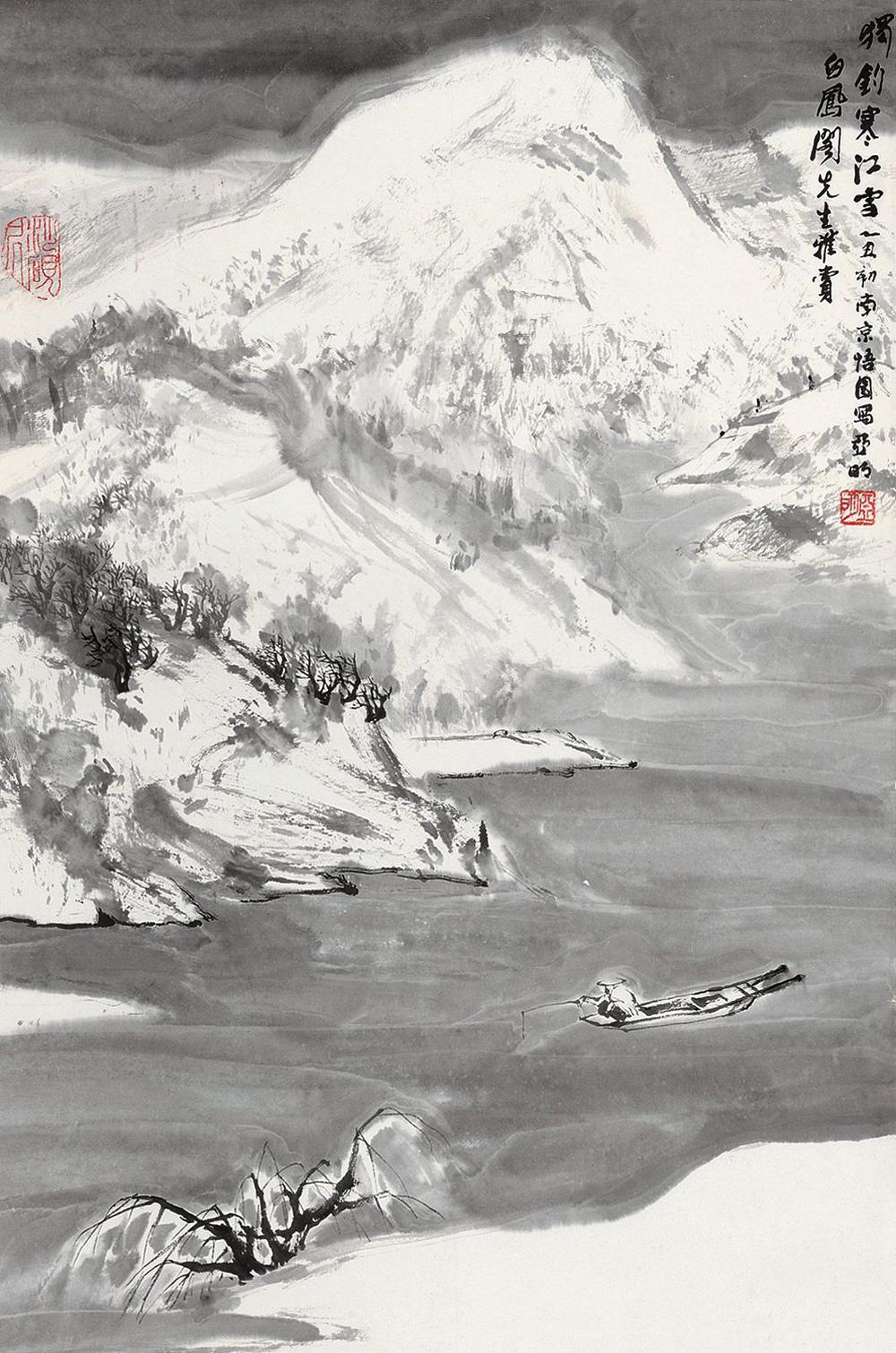褚師三憶
李金坤 2022/01/06
2006年11月1日,那是一個令人哀慟萬分的日子。就在此日,北京大學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褚斌傑先生不幸逝世。光陰荏苒,而今,褚先生離開我們已整整十年了,但是在這期間,先生的音容笑貌則時時像電影似的映現於我的腦屏心幕之上,先生的人品學品亦每每溫潤我懷,令我感動不已,感念不息,感佩不止,感恩不盡。褚先生留給我的記憶太多太深了,限於篇幅,茲就先生對我影響最大、印象最深之三事略作回憶,以聊表對恩師的追思與悼懷之情焉。
一、鴻雁蘊真情
八十年代初,我有幸從中學調入縣電視大學任教,擔任漢語言文學專業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輔導教師。當時電視大學課程的主講教授,都是由中央電視大學聘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科院等名師擔任。北京大學褚斌傑先生,即擔任《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主講教授。我每次隨堂聽課,都被電視中褚先生那春風滿面、和藹可親的形象與舉重若輕、深入淺出的講解所深深吸引,使我又一次享受了極為難得的高品質的大學中文專業的教育機會,甚感快樂與幸福。從此,褚先生的名字便深銘於我的心中。
由於學校圖書條件的限制,因此我在輔導該課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總是難以解決,頗感惆悵與鬱悶。萬般無奈之下,我想直接請教褚先生。但轉念一想,褚先生是北大名教授,教研任務甚重,而我則是與褚先生素昧平生且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教師,豈敢貿然打擾先生?然而,問題的難路虎卻橫梗面前,使我身心困擾、寢食難安。思來想去,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高度責任感,遂激發我勇敢地拿起了筆,斗膽向褚先生寄去了第一封求教信。信雖然發出去了,但我則忐忑不安起來,似有一種惶恐難測的渺茫之感。誰知,就在我疑惑不定之際,發信後的第六天,我即收到了褚先生的回信。褚先生不僅圓滿回答了我的全部問題,而且還複印了有關材料供我參考。末了,褚先生還為有我這樣虛心求教的“助教”而感到高興,並且感謝我這個“助教”為他這個“主講”教授解決了實際問題。我面對如此樂於助人而又虛懷若谷的褚先生之回信,不禁潸然淚下,滿腦子盡是“感動”、“感激”的詞彙在交替浮現。想不到作為名校名師的褚先生,竟如此熱情友善、滿懷真情,直令我頓生“遇上貴人”的喜悅之情。此後,除了向褚先生請益教學問題外,大凡有關我研究之設想、工作之困惑、前程之憂慮等問題,都一一向褚先生彙報請謁,而他總是不厭其煩,每信必復,給我以精心指點與熱心開導。即使在他患有嚴重的高血壓病期間,對於我求教信的回復也從未間斷。在褚先生給我幾十封信的“寄信人地址及姓名”欄中,先生一律寫著“北京大學暢春園52樓409號褚緘”的字樣,直到前幾年先生喬遷新居為止。暢春園,是一個多麼值得記憶多麼令人神往的溫馨之地啊。正如其園名“暢春”所示,褚先生對我無私而熱情的關懷猶如怡暢心扉的三月春風,使人倍覺無比溫暖。
為寫作此文,日前我將褚先生給我的所有回信又細讀一過。捧讀這些信件,猶如和煦春風撲面來,暖我心胸暢精神,字裡行間充盈著一位學術名師對年輕後生的無微不至的關愛與策勵之深情。在一封信中,褚先生如此熱情地寫道:“看到你的著作目錄,你的確很用功,寫了不少論著。我看搞古代文學,也沒有多大條件限制,不外是讀、思、寫而已,常用書備一些也就行了。你參與縣誌工作,搞地方文化倒是個好條件,如來信所述,不妨在這方面做些研究,正是別人所難及指處。”既有熱情的鼓勵、切實的指導,又有客觀的分析、精闢的見解,給我影響甚大。有時,在先生那些看似自然輕鬆的文字中,總是流露出似淡實濃、耐人尋味的夫子自道的深厚情味來。在一封信的結尾,先生這樣寫道:“天氣漸暖,江南水鄉,風物佳麗,當已另番景象;北方仍在春寒之中,特別是北京,每至春天就刮大風,身體也不好,故很少外出,蟄居斗室,看些雜書自娛而已。”透過這些清淡如茶的語言,我們不難感受到先生那種不畏天寒老病、依然勤學不輟的只爭朝夕之執著精神。是啊,褚先生硬是憑仗這種爭分奪秒、刻苦奮鬥之精神,千方百計地去彌補過去非常時期對自己所造成的嚴重的學術研究之損失。在粉碎“四人幫”到先生逝世的近30年的時間裡,褚先生以頑強的毅力抗爭著嚴重的高血壓等疾病,發表了《中國古代文體概論》、《中國古代文學綱要》(一)、《中國古代神話》、《白居易評傳》、《古典新論》等十餘部專著及百餘篇論文;在擔任繁重的本科教學任務的基礎上,精心培養碩士、博士、博士後及訪問學者、進修生等高級人才數十人;同時還擔任著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等國家級學會的領導與組織工作,對中國的學術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重要貢獻,真可謂黃昏奮蹄、鞠躬盡瘁焉。此時此刻,拜讀褚先生信中那清秀雅重的文字,只覺一股股真情暖流遍全身;而我,惟有銘記褚師恩,寸草力報春暉情。
二、訪學見摯情
九十年代伊始,我有幸調入江南某高校任教。為了擴大自己的知識面,提高教學水準,以適應飛速發展的高教形勢之需要,我想到北京大學跟隨褚斌傑先生做高級訪問學者。因為有了向褚先生請教多年、深得厚愛的感情基礎,我寫信向先生談了自己的想法,先生立即回信,表示非常歡迎我隨其訪學。就這樣,我由原來電大“主講”教授褚先生的“助教”身份,成為褚先生的入室弟子——高訪學者。在這脫產學習的一年裡,遇到問題,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樣寫信向先生請教,可以面對面地親聆先生教誨了。為此,褚先生甚為樂意,而我則更是萬分喜悅。此前,我只是在電視上見過褚先生,直到這次訪學,我才得以一睹先生尊容。先生身材高大,面容較之電視所見似乎更為清臒,然卻精神矍鑠,藹然可親。先生談吐幽雅,笑聲清朗,面對先生,如沐春風。
訪學期間,在褚先生全面而熱情的指導下,我不僅完成了《風騷比較新論》專著初稿的寫作,而且完成了由褚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詩詞精品鑒賞》“近代詩詞”部分20餘萬字的撰稿任務。此外,還選修了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吳小如、費振剛先生的詩經學、張少康先生的文論學、葉朗先生的美學、袁行霈、葛曉音先生的唐詩學、陳平原先生的小說學及海外著名學者如陳抱一等先生的專題學術講座等具有一流學術水準的課程。置身北大這座具有優良傳統的學術天堂裡,我猶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與飛翔花林的蝴蝶一樣,總是不知疲倦、夜以繼日地奔波穿梭於教室、講堂與圖書館之間,如饑似渴地吮吸著古今中外的知識瓊漿。如此求學的火熱之情,除了我原有的向學之志的激勵外,主要還是我親受褚先生置老病於度外而日夜枯坐書齋鑽研不已可貴精神的感染。每次,我去請教褚先生,總見他滿案是書,或開或合,或折或疊,潛學之景,動人心魄。尤其感人的是在炎夏季節,褚先生於暢春園住在頂樓,樓為平頂,太陽直射,室溫甚高,加之空調品質欠佳,降溫效果不夠理想。在這樣坐著都冒汗的書房裡,褚先生卻依然讀研不止,樂在其中。先生這種固守斗室、執著科研的頑強精神,極大地鼓舞了我的求學之志。後來,先生在《風騷比較新論》拙著所作序言中評價我的訪學表現時說道:“訪學期間,李君心無旁騖,選課(共選修碩士、博士課程十餘門,遠遠超過規定要求)、讀書、聽講座,廣采博納,全力‘充電’,誠篤敦厚,勤勉好學,並著手從事《詩經》與《楚辭》的比較研究。”我之所以能夠這樣,完全是因為先生忠誠學術之精神對我鼓舞的結果。我打心眼裡欽佩褚先生,感激褚先生。
在親受先生教誨的過程中,褚先生十分真誠地傳授讀書與科研之法,金針度人,毫無保留。先生常說,做學問,搞研究,無非是材料要真、方法要新、觀點要明三者而已;切忌隨人後,炒冷飯,湊拼盤;與其修補大廈,不如另砌茅屋。先生甚為注重學術研究的創新價值與意義,其一版再版、屢獲大獎的開山名著《中國古代文體概論》,便是這方面最好的榜樣。此外,褚先生還告誡我說,做學術爭鳴與商榷類的文章時,要以理服人,寬厚諒人;不要以勢壓人,出口傷人。體現了先生一以貫之的對古今學人所抱有的同情之理解的寬人律己、敦厚睦好之學術風格。記得有一次,我做了一篇與當代某楚辭學者商榷的文章,文中指名道姓,言詞激烈,冷諷熱嘲,火氣頗大。小文面呈褚先生面審後,即建議我將那些充滿火藥味的文字全部刪去,甚至連姓名都無需提及。接著,褚先生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學術爭鳴,在無權威定論出現之前,我們都不能輕易肯定誰或否定誰。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誰對誰錯,自有公認”。褚先生這種以誠待人、友好爭鳴的和諧學術風範,在學術界是有口皆碑的。而作為親聆謦欬的入室弟子,我受其影響則自然是直接而深遠的。
三、作序寓深情
在北大做高訪一年,我的收穫是很大的。除了聽取國內外許多名師的專題學術講座、與導師褚先生合作完成了有關科研專案外,還初步撰成《風騷比較新論》拙著,這是我隨褚先生訪學的重要成果之一。北大訪學結束後,我遵照褚先生的具體意見,花了幾年時間,對拙著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增刪修改。訪學初定下拙著這個題目時,褚先生就甚為贊許。認為拙著在中原文化與南楚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背景下進行《詩經》與《楚辭》的全面比較研究,是一項具有開創性、集成性的全新工作,意義重大,希望我認真做好,並主動提出要為拙著作序。在整個研究過程中,褚先生對拙著綱目的設置、材料的收集、方法的運用、觀點的提煉等方面,都作了全面而切實的指導,先生為此傾注了不少心血。當我把拙著將要出版的消息告訴褚先生時,他極為高興,囑我趕快將清樣寄他,以便寫序。拙著是《詩經》與《楚辭》比較之研究,而褚先生是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拙著能得褚先生作序,無疑是件極其難得之幸事。但我後來才從方銘兄處獲悉,其時褚先生已患絕症,且已處於二度化療階段,可此前先生卻未漏一絲風聲。先生重病在身,不能作序,於情於理,作為學生的我來說,無論如何都是十分理解的。可是他卻隻字不提,還讓他的家人一起瞞著我,毅然堅持為我作序。先生啊,先生,到了如此地步,您還是一如既往的為他人著想,這種忘我樹人的崇高品德,怎不使我感激涕零,羞愧難當!我實在不忍心讓先生在這樣的情形下寫序了。我知道,先生允人之事,是從不食言的。不讓作序,他是絕不會同意的。我就委婉地換了一種說法,告訴他,序總是由先生寫,拙著不急出版,待先生康復後寫序不遲,現在養病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我以為這樣就能讓先生安心養病了。誰知,先生還是在化療過程中堅持寫完了序。我清楚記得,先生在電話的那頭,以低微的聲音對我說,要不生這個病啊,序會寫得更從容更深入一些﹍﹍。聆聽師言,電話這頭的我早已是淚流滿面、泣不成聲了。先生啊,先生:您的峻潔人格如高山,您的仁厚美德似大海,您的謙讓作風像青松,您的奉獻精神同翠柏。正所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褚師厚我情。
拙著如期出版了,許多讀過褚先生序言的朋友都說,序言寫得誠實中肯,評價到位,慧眼獨具,語樸情深,是時下難得之佳序。先生序中如此評價說:“李君在中原文化與南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上重新審視《詩經》與《楚辭》之關係,體現了他敏銳的學術眼光和孜孜不倦的學術追求。像李君將《風》與《騷》作系統整體研究並撰成專著者,目前尚未幸見。李君此項研究是甚有學術價值與意義的。”我知道,褚先生給予拙著如此高的評價,完全是出於對我的鼓舞、鞭策與呵護。此外,先生對拙著的創新之處、研究方法與個人素養等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殊不知,這是先生在他生命的垂危時刻,用他全部的精力與關愛鑄成的驚心動魄的最美文字,也是先生整個學術生涯的感人肺腑的精彩絕唱!它不僅是褚先生對我個人學術事業的獎掖、鼓勵與厚望,而且也代表了德高望重的老一輩學者對年輕一代學術研究的褒揚、激勵與希望。先生殷殷之情,後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後來,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便沿著自己《風》《騷》比較的研究格局與路徑,完成了博士論文《風騷詩脈與唐詩精神》。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將《風》《騷》精神對唐詩的影響作了頗為全面而深入地探研,開創了《詩經》、《楚辭》與唐詩研究的新領域,彰顯了《詩經》、《楚辭》這中國詩歌兩大源頭的藝術精神之無窮魅力。博士論文受到了評審專家與答辯委員們的一致好評,不久又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專案的支持。現在,四十萬言的博士論文已經正式出版。撫書思人,褚先生當年親自指導我做《風》《騷》比較研究的動人情景便油然映現腦際。沒有北大隨褚先生高訪的經歷,沒有褚先生的傾情引導,就沒有我今天的學術成果。每念及此,我便情不自禁,潸然淚下。褚先生倘若九泉有知的話,一定會為我博士論文的出版而頷首微笑、甚感欣慰的。
在褚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學生要回憶的往事很多,要感謝的話語難盡,謹此特草擬小詩一首,聊表對恩師褚先生的感戴之情。詩曰:
中央電大遇褚師,從此結緣卅載怡。
魚雁來回勤解惑,暮朝叩訪細排疑。
未名博雅銘情厚,蕙李桃蘭沐善齊。
德劭品高同日月,心香一瓣寄哀思。
(李金坤:江蘇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