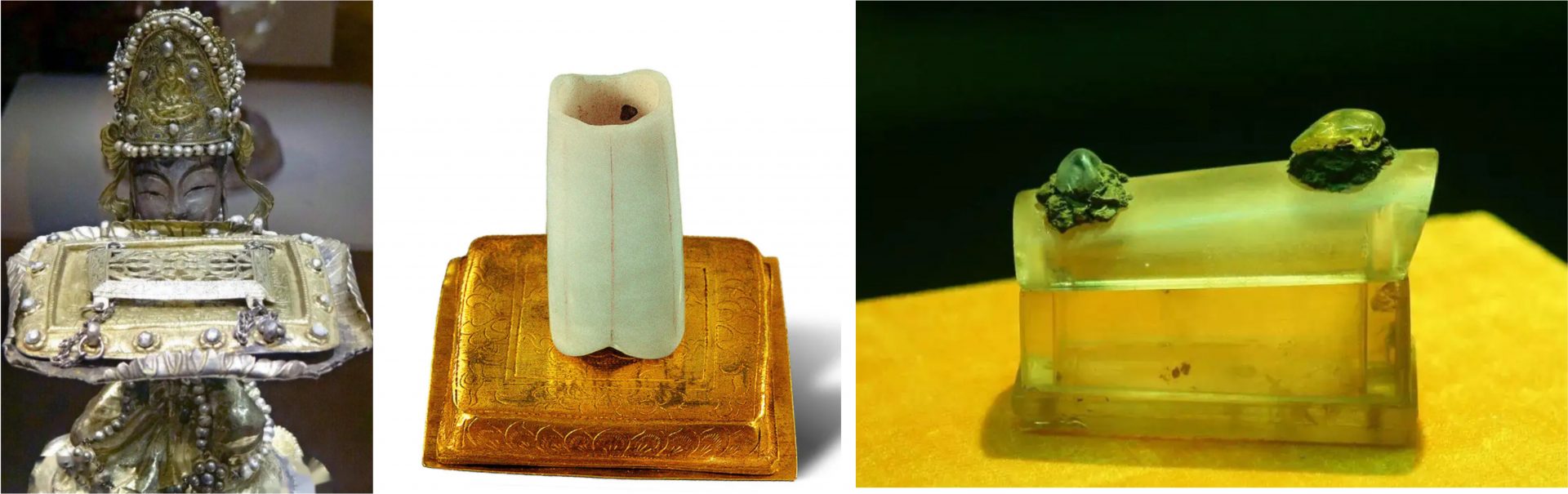第三章 元和新政
自永貞元年(805年)七月二十八日主持軍國之事,憲宗開始掌握大唐帝國的最高權力。執政以後,憲宗在進一步採取措施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基礎上,以貞觀、開元之政作為自己效法的榜樣,在內政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並取得顯著的成效,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元和新政”,為“元和中興”打下了重要基礎。
第一節 調整人事 貶黜 “二王”
一 倚以腹心之任
在貞元末年的政治鬥爭中,憲宗依靠部分宦官、方鎮和朝官的支持,很快登上了權力的最高峰。嗣位伊始,憲宗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朝廷中的政治力量進行重新配置,提拔安插了一批政治上擁護自己的朝臣,牢牢控制住朝廷的機要部門。同時,對以“二王”為首的政治反對派進行清洗。
永貞元年(805年)七月二十八日,憲宗掌握軍政大事的同時,通過俱文珍等宦官出面陳請,以順宗的名義將杜黃裳、袁滋、鄭珣瑜、高郢等一批官員授以重職。[1]
首先,任命杜黃裳為門下侍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命袁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進士出身,登宏辭科。最初杜黃裳任郭子儀朔方從事,郭子儀入朝後,他主持朔方軍務。德宗時任侍御史,由於受裴延齡排擠,曾在貞元時期十多年中不得升遷。王叔文等掌權後,杜黃裳雖被任為太常卿,但他反對王叔文等人的所作所為,從不登王叔文之門。杜黃裳曾勸“二王”之黨、自己的女婿、身為宰相的韋執誼率領百官請求太子李純監國,韋執誼卻說,丈人才得一官,怎能輕議禁中的事呢!杜黃裳因此大怒,稱“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2] 拂袖而去。由於杜黃裳是“二王”集團的反對派,又堅決主張惶太子監國即位,且資歷深厚,憲宗將其提拔為宰相,用意是十分明顯的。
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歷任詹事府司直、侍御史、工部員外郎、華州刺史等職。享有治民寬易清簡的盛名。貞元十九年(803年),袁滋代表朝廷從西川出使南詔,與西川的韋皋關係十分密切。韋皋在西川極力主張太子監國,與袁滋的聯絡鼓動有關。因此,憲宗監國後,不忘韋皋、袁滋的擁立之功,任袁滋擔任了宰相。[3]
同時,憲宗還以順宗的名義任命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鄭珣瑜因與王叔文的政見不同及王叔文的無禮而辭去相位,屬於“二王”的政治反對派。憲宗既然是以順宗的名義任命官員,不便於再任鄭珣瑜為宰相,因而任命其擔任了吏部尚書。表面看官職似乎不如過去,其實則是以鄭詢瑜牢牢掌管官吏任命大權。[4]
高郢,字公楚,渤海(今黑龍江一帶,唐時為靺鞨族居住地)人,高郢少年時即以願替父受死而著名,後來進士及第,歷任華陰尉、副元帥判官等職。德宗時更以不懼刀斧反對李懷光叛亂而名聞天下。順宗時任禮部侍郎,主持考試。高郢嫉惡浮華風氣,拒絕請托,即使是同事熟人,也從不在考試上有半點通融,因而受到韋執誼等人的嫉恨,也屬於“二王”集團的政治反對派。[5]憲宗任高郢為刑部尚書,又掌握了司法大權。
憲宗初監國,便掌握了中書的決策權、門下的封駁權,而吏部“銓綜為選士之本”,刑部“刑法及生人之命”,[6]這就為憲宗進一步鞏固政治地位奠定了基礎。
永貞元年(805年)八月,憲宗正式即位後,以皇帝的名義繼續在人事上加以調整:八月二十七日,任命鄭余慶為平章事,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命鄭絪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鄭余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今河南榮陽)人,進士出身,貞元初年已任翰林學士,貞元十四年(798年)出任相職,後來因故被長期貶為地方小官。憲宗拜命他為宰相,一方面因他是德宗時舊臣,貶後復起,必會感恩效力,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其叔父鄭絪立有擁立之功,從中薦舉的結果。[7]
鄭絪,字文明,鄭余慶的叔父。幼有奇志,進士出身。德宗時任起居郎、翰林學士。順宗召鄭絪起草《立太子詔》,鄭絪徑直書以“立嫡以長”,表明了他堅決支持憲宗的政治態度。其後,《冊太子文》、《太子勾當國事詔》、《即位赦文》等,大都出自鄭絪之手。[8]憲宗任其為宰相、顯然帶有報答其擁立之功的意味。
此外,元和初年(806—809年)憲宗重用的武元衡、裴均、竇群等人,也都是“二王”集團政治上的反對派。武元衡,字伯巷,河南緱氏(今河南偃師南)人,曾祖是武則天的從父弟。武元衡進士出身,歷任監察御史、華原縣令、比部員外郎、左司郎中等職。順宗即位時,武元衡任御史中丞,王叔文曾以權利爭取武元衡的支持,沒有成功。後來武元衡擔任德宗山陵儀仗使時,又與“二王”集團的重要成員劉禹錫發生矛盾,幾天後武元衡被貶為右庶子;憲宗冊封皇太子時,武元衡擔任贊引。憲宗為太子後,與武元衡多有交往,“知其進退守正”,[9]所以憲宗登極,恢復武元衡的御史中丞之職,元和二年(807年),憲宗又以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並兼職管理重要的戶部事宜;
竇群,字丹列,扶風(今陝西扶風)人,本人出身布衣,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後經人推薦,擔任了左拾遺、侍御史等職。王叔文集團的柳宗元、劉禹錫頗看不起竇群的為人,竇群亦公開與王叔文等人作對,曾當面譏諷王叔文會落得貪官李實的下場。憲宗即位後,一方面因為竇群的政治態度,另一方面由於于頔、武元衡等人的大力推薦,憲宗任竇群為御史中丞。[10]
對於在永貞年間曾起過重要擁戴作用的荊南節度使裴均,憲宗即位以後本想立即重用,但裴均有著“沾汙台輔”的不佳名聲,自己又妄自驕矜。有一次入朝時曾越位而立,受到朝官盧坦等人諷刺,憲宗事後貶了盧坦的官職,但考慮到朝官們的態度,還是沒有馬上任裴均以重職。元和三年(808年),憲宗方授裴均為右僕射,並擔任了使相.即使如此,憲宗的這一任命,仍使“外議紛然”。[11]
大體來看,元和初年(806—809年),憲宗在人事上的一系列安排與調整,主要是安插永貞年間政治鬥爭中支持過自己的一批官員和親信。這些官員和親信的提拔,固然也視其才能如何,但更主要的則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態度。憲宗對他們的重用顯然是要使自己的政治基礎更加牢固。元和初期以後,隨著權力的穩固,憲宗在用人的問題上,才更多地側重於官員的德才兼備、真才實學了。
除了朝官以外,元和初年,憲宗對宦官集團也進行了一系列調整。
[1] 《舊唐書》第14卷,第409頁。
[2] 《舊唐書》第147卷,第3973頁。
[3]《舊唐書》第185卷,第4830頁。參見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冊,第七章,第338頁。
[4]《新唐書》第165卷,第5064頁。
[5]《舊唐書》第147卷,第3976頁。
[6]《唐大詔令集》第55卷,第266頁。
[7]《舊唐書》第158卷,第4163頁。
[8]《舊唐書》第159卷,第4181頁。
[9]《舊唐書》第158卷,第4160頁。
[10]《舊唐書》第155卷,第4121頁。
[11]《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53頁。
法門寺地宮典藏文物
二、貶黜“二王”集團
在提拔和重用擁戴功臣等自己的政治勢力的同時,憲宗對自己的政治對手王叔文、王伾集團,給予了徹底的清除與打擊。
永貞元年(805年)八月五日,順宗剛剛禪位於憲宗,八月六日,憲宗便發出《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參軍制》,其文曰:
銀青光祿大夫守散騎常侍翰林學士上柱國富陽縣開國男王伾、將仕郎前守尚書戶部侍郎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副使賜紫金魚袋王叔文等,夙以薄伎,並參近署,階緣際會,遂洽恩榮。驟居左掖之秩,超贊中邦之賦。曾不自厲以效其誠,而乃漏洩密令,張惶威福。畜奸冒進,黷貨彰聞。跡其敗類,載深驚歎。夫去邪厝枉,為國之要,懲惡勸善,制政之先。恭聞上皇之旨,俾遠不仁之害,宜從貶削,猶乎優容。伾可開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叔文可守渝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並馳驛發遣。[1]
從制文的主要內容來看,憲宗所列“二王”的主要罪名有三條:第一,以薄伎因緣際會,得到時為太子的順宗的信任。所謂“薄伎”,是指王伾初職為侍書待詔,王叔文初職為以棋待詔。第二,輕易得到宮廷高官,不自檢點,漏洩密令。第三,張惶威福;畜奸冒進,贖貨彰聞、跡其敗類。
從制文所列“二王”的罪行來看,其實是非常空虛的。三條罪狀中,似乎只有“漏洩密令”幾句是較為實在的東西;但具體“二王”洩漏了什麼密令,仍不得而知,大概是指“二王”對外人講起過順宗什麼密令之類。“蓄奸冒進”,則是批評“二王”大膽起用後起之秀的事。“黷貨彰聞”則應是指王伾好貪貨賄的傳言,而這些傳言大多出自政敵之口,並無多少根據。[2]
不管怎樣,憲宗現在已處於執政的地位,即使列不出什麼像樣罪狀來,要貶黜“二王”等人,反對派也是無法講什麼了。九月十三日,憲宗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3]
十一月,憲宗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韋執誼因為曾與王叔文有矛盾,其丈人杜黃裳現又為宰相,因此憲宗對他的貶黜,拖了一段時間。自從王叔文失敗,韋執誼“自失形勢,知禍將至,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4]
十一月,許多朝官認為對王叔文之黨,從員外郎貶為刺史,貶黜太輕,向憲宗提出應加重處理。於是憲宗在十一月十四日,再次下令,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淩准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異為郴州司馬。在貶黜韋執誼及韓泰等人的制文中,憲宗重點指斥的是“朋黨比周,挾邪敗度”的問題,[5]說明憲宗主要還是將“二王”集團視作一個政治上的敵對勢力來看待的,至於他們具體犯有哪些罪行,憲宗是不在意也不必在意了,只要這個集團曾反對過自己,這一點就足夠了。
被貶以後的“二王八司馬”,按憲宗的詔令,將終身不復起用。王叔文在遭貶後的第二年,被憲宗下令處死。王伾赴貶所之前已經中風,到開州不久便病死貶所。韓曄貶為饒州司馬,量移汀州刺史,死於永州。陳諫由台州司馬任封州刺史,在通州去世。
憲宗雖然規定“二王八司馬”“逢恩不原”,其實為了適應政治的需要,元和四年(809年)即開始起用程異參預漕運工作,擔任揚子留後,後來又加以重用提拔。劉禹錫也曾於元和十年(815年)被召回京,朝廷擬重新授官郎署。劉禹錫次年作了《遊仙都觀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載。[6]
劉禹錫借桃花比喻那些由於投機取巧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貴,以看花人比喻那些趨炎附勢、攀高結貴之徒,並不屑一顧地指出,這些人不過是我被排擠出朝廷後被提拔起來的罷了。
劉禹錫此詩一出,得罪了權貴,也激怒了憲宗。憲宗下令將劉禹錫貶為播州(今貴州遵義)刺史。詔書下達後,御史中丞裴度奏稱劉禹錫家有八十歲老母,請憲宗能給予照顧。憲宗仍怒氣不解地說,“夫為人子,每事尤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7]不過,事後憲宗還是考慮到劉禹錫的實際困難,將其任為較近的連州(今廣東連州)刺史。直到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劉禹錫才又回到朝廷。劉禹錫前事不忘,又作《再游玄都觀》一詩,以“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8]表達自己矢志不悔的決心,當然這是後話了。
柳宗元被貶以後,元和十年(815年),量移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逝於柳州。韓泰後來量移漳州刺史,又遷郴州刺史。淩準則死於連州。韋執誼死於崖州。
一方面憲宗毫不留情地清除了王伾、王叔文集團,[9]另一方面,憲宗對父親順宗自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十六日即位到七月“二王”失敗這一百五十多天中所取的改革成就,卻予以客觀地承認。只不過憲宗是將所有的成績都記在了父親的名下。儘管憲宗在為“二王八司馬”羅織罪名時頗感荊手,而當他需要為父親歌功頌德時,卻十分輕易而具體地擺出了一系列的政績。
元和元年(806年)七月十一日,憲宗在安葬父親順宗於豐陵之際,發佈《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諡議》,文中稱順宗“奄宕穴以搜賢才”,“黜進獻以藝貢賦”。“滌疵瑕而復放竄”,“蠲逋責而惠困窮”。[10]在稍後的《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哀冊文》及《順宗加諡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議》中,[11]憲宗對父親的功業更不惜筆墨,進行了全面總結。除了提到順宗為太子時輔佐德宗的功績外,重點指出了順宗執政一百五十多天中的業績,主要有:任用賢才,起用流亡;省刑恤隱,蠲除逋欠;減去宮人,斥絕奇貢;黜罷酷吏,遠近悅服。
對比貶黜“二王八司馬”空洞的制文,憲宗在《諡議》中所列父親順宗的業績,就不再是以浮言歌功頌德了,而都是確有所指,十分具體的。從諡議的內容來看,順宗不再是“久疾不任政事”、“厭倦庶政”,[12]而是一個勤於政事、勇於改革的帝王了。
很明顯,從對順宗執政時期政績的肯定可以看出,憲宗並不反對父親順宗執政時所進行的種種革新,只不過是憲宗將所有的成績全部加在了父親的頭上,而當時具體執行順宗政令、進行改革的“二王”集團,卻仍被斥責為“畜奸冒進,不自檢點”的小人。
在中國古代社會裡,君臣父子必須以忠孝為本,無論父皇在位執政期間具體情況怎樣,作為兒子的一般只應歌功頌德,而不允許有所指責。憲宗自然也不能脫離這一傳統道德的規範,更何況父皇確有政績可稱呢。既然要稱讚父皇,就必須將順宗與“二王”等人區分開來,歌頌的只能是父皇,這既是由於傳統道德的約束,也是維護自己統治,掩飾永貞年間(805年)自己與父親權力鬥爭真相的一種需要。
從憲宗充分肯父親順宗政績這一事實說明,憲宗並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並不反對對祖父德宗後期以來的種種弊政進行改革。憲宗與“二王”集團之間的鬥爭,不是改革與反改革之間的鬥爭,而是統治階級內部爭奪權力的鬥爭。憲宗對“二王”集團的打擊,不過是政治鬥爭的一種需要。將憲宗打擊“二王”集團等同於反對改革、打擊改革運動,實際並不正確。自憲宗登基以後,他開始了遠比父親更大範圍、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改革,元和中興的局面隨之到來。
[1] 《冊府元龜》第153卷,第1851頁。
[2] 如《舊唐書》第135卷,第3736頁載,王伾家中有無門大櫃,只開一洞,以投納賄金寶,王伾妻睡臥其上。顯然言過其實。
[3]《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22頁。
[4]《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22—7633頁。
[5]《唐大詔令集》第57卷,第278頁。
[6]《全唐詩》第365卷,第912頁。
[7]《舊唐書》第160卷,第4211頁。
[8]《舊唐書》第160卷,第4212頁。
[9] 與以往列祖列宗的做法不同,憲宗在打擊政治反對派時,並沒有採取斬盡殺絕的做法。
[10] 《大唐詔令集》第13卷,第69頁。
[11] 《舊唐書》第14卷,第418頁。
[12] 《舊唐書》第160卷,第4210頁。
法門寺地宮典藏文物
第二節 孜孜以求 探索治道
一、追二祖道德風烈,樹良好君臣關係
如何治理天下?怎樣處理君臣之間的關係?怎樣發揮臣下的作用?這些問題,憲宗在正式即位以前已有所考慮,並且表露出自己的觀點。溵水之敗,韓全義不見德宗而歸鎮,憲宗當時對這種“敗法亂禮”的現象就極為憤慨。[1]對於祖父對藩鎮強臣的姑息,憲宗也有著自己的看法。對於“二王”集團執政時期的君臣關係,憲宗更是深為不滿。即位以後,怎樣處理君臣關係,如何治理天下,這些問題,更加現實地擺在了眼前
總的來看,憲宗對自己執政所要達到的目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就是要“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即“弘開元之治”,因避高宗李治之諱,所以改“治”為“理”),“舉貞觀、開元之政”。[2]憲宗執政期間曾反復地強調這一問題。還在元和初年,憲宗就曾盛讚太宗、玄宗之治,並對翰林學士李繹說:“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諡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李絳回答:“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憲宗聽了李絳所言,深表贊同:“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3]
李絳的進言包括許多方面,首要的則是憲宗自己要正身律己,尊祟傳統的道德,其次是要注意用人,進忠直,遠邪佞,注意君臣關係。其餘尚有吏治問題、擇將問題。法令問題、戒奢問題等,李絳認為,這些方面如果都能說到做到,實現中興,並不久遠。事實證明,元和年間,憲宗是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的。
憲宗認為,在君臣關係上,人主應推誠,人臣應盡忠,上不疑下,下不欺上,君臣一心,各司其職,方能使國家達於大治。在這一問題上,憲宗多次與大臣們進行討論。
元和元年(806年)二月十八日,憲宗向宰相們提出,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兩者互有得失,怎樣做才是最恰當的呢?杜黃裳回答說:帝王對上承受著天地與國家賦予的使命,對下面負有安撫百姓與周邊民族和邦國的重任,朝夕憂心勞苦,當然不能夠自圖清閒,自求安逸。然而君主與臣下,是各有職分的,國家的法度也是有一定程式的。如果君主能夠慎重地選拔天下賢才,並且將重任託付給他們,當他們立功的時候予以獎賞,當他們犯罪的時候,給予處罰,選拔與任用都出以公心,獎賞與懲罰都不失信用,那還會有什麼人不竭盡全力為朝廷辦事呢?朝廷還會有什麼尋求的目標不能實現呢?
杜黃裳特別指出了帝王勤勉操勞與清靜無為的關係,認為賢明的君主在尋求人才時是勤謹辛勞的,而在用人之後,則應放手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才能,各司其職,君主不具體過多地干預,相對清靜安逸。這便是虞、舜既清靜無為而又使政治修明的原因。杜黃棠又列舉秦始皇、魏明帝、隋文帝不信任臣下,事必躬親,最後導致君臣猜疑,國亂民怨,被後人恥笑的事例進一步說明君應推誠、臣應盡忠的道理。
實際上,無論是憲宗還是杜黃裳,都知道在君臣關係上,還有更為直接的教訓可以吸取,那便是憲宗親眼所見到的祖父德宗與群臣的關係。德宗皇帝自貞元後期以來,“不任宰臣以事,人間細務,多自臨決,裴延齡等得以奸進,而登臺輔者,備位而已。”[4]結果導致貞元後期政治敗壞,君臣關係緊張。憲宗早年對此“心固非之”,[5]杜黃裳又一次提出這一問題,進一步引起憲宗的注意和重視;
元和初年的談話,對憲宗在元和年間的執政方針有重大影響。“杜黃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上心,上既聞黃裳之言,聳聽延納”,於是“選擢宰相,推心委之”。憲宗曾在元和三年(808年)九月,感觸很深地說:“乙太宗、玄宗之明,猶籍輔佐以成其理,況如聯不及先聖萬倍者乎。”[6]在憲宗看來,貞觀、開元年間的君臣關係是最值得學習和效法的。貞觀、開元的政治經驗,值得學習的最多,由此憲宗即位以後,遍讀列祖列宗《實錄》,尤其愛不釋手的是《太宗實錄》、《玄宗實錄》及《貞觀政要》。
為隨時提醒自己處理好君臣的關係。元和四年(809年),憲宗詔令李絳、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人搜集歷代君臣成敗經驗五十餘種,並親自編選成《前代君臣事蹟》十四篇,手書於六張屏風之上,宣示臣下,激勵自己。每次觀覽前代興亡得失,都三復其言,[7]始終把貞觀、開元之治作為自已執政奮鬥的目標。
總的來看,憲宗在元和年問(805—820年)比較好地處理了君臣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注意充分發揮臣下的作用,因而終於平定了藩鎮,取得了“元和中興”的功績。
[1]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20頁。
[2] 《舊唐書》第164卷,第4286頁。
[3] 《新唐書》第152卷,第4836頁。
[4]《唐會要》第53卷,第916頁。
[5]《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54頁。
[6]《唐會要》第53卷,第916頁。
[7]《唐會要》第36卷,第660頁。
法門寺地宮典藏文物
二 虛心求諫納諫、形成批評風氣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是貞觀年間(618一640年)魏徵多次向唐太宗提出的問題。虛心求諫納諫,廣採群臣意見,這是太宗實現“貞觀之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憲宗執政期間特別是平淮西以前,對這一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並形成自己的特點:
首先,將能否求諫納諫,當作能否實現天下大治的重要問題來對待。
對此,憲宗有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元和初年,憲宗忙於政權的穩定及各種政務,一時尚未顧及求諫納諫的問題。朝廷雖設有左拾遺、右補闕等諫官,實際上並不能正常發揮作用。以至於憲宗在永貞元年(805年)八月即位到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半年多的時間裡,一次也未曾召見過諫官,[1]為此,四月下旬。左拾遺元稹上書,向憲宗論述諫職及求諫、納諫的重要性。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陽人。生於長安,自幼喪父,家庭貧困隨母刻苦自學。十五歲明經及第。元和元年(806年)舉制科,對策第一。作為左拾遺,元稹在疏文中指出: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曾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宮,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改,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郜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劃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命,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語,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盡所懷,豈可置於其位而屏棄疏賤之哉![2]
元稹的疏文一方面陳述了貞觀年間(627—640年)太宗皇帝對諫官的重視,認為重視進諫是當時天下大治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批評了當今諫官不能參與時政,只是排行就列、朝謁皇帝的不正常現象。元稹還特別指出近年以來,上牙不奏事及庶官罷巡對的問題。上牙指皇帝召見群臣的正殿。貞元十八年(802年),德宗在含元殿上朝,嘉王府諮議高弘本上奏,自訴拖欠租稅之事。德宗為此很不高興,詔令自今公卿庶僚不許在正殿奏事,如有陳奏,在延英門請求詔對。此詔一出,當時就有大臣認為,正牙奏事,自高祖以來就未曾改變過。之所以堅持下來,主要是為了下情上達,討論政事。高弘本無知,可以降免其職,不能因人而廢事。[3]但是當時德宗既不信任臣下,更不喜歡在大堂之上聽取意見。高弘本之事不過是德宗取消正牙奏事的藉口而已。自貞元十八年(803年)至元和三年(808年),五年以來,正牙奏事制度一直沒有恢復。
所謂庶官巡對,原是貞元七年(791年)時德宗開始設立的,每天由值班官引見二名官員,聽取他們的意見,有重要者,轉奏皇帝, 這樣可以保持皇帝與朝官的廣泛聯繫,對於改進朝政是有益處的。但貞元末年以來,這種制度也被德宗取消了。
元稹認為,諫官既不能在正殿奏事,又沒有機會向有關官員彙報意見,因此只有上書奏事一路。但是元稹指出,朝廷大事,君臣之間,在事情發生或詔令頒佈以前,臣下雖婉言規勸、周密謀劃,尚且難以回轉皇帝之意,況且詔誥已經頒佈,命令已經執行,要想憑著諫官的一紙章奏改變皇帝的成命,實在也太困難了。元稹建議,憲宗應常在延英殿召見諫官,專門聽取意見,不應安置了諫官的職位而又不聽取他們的意見,甚至疏遠賤視他們。[4]
時隔不久,元稹再次上疏進一步陳述進諫的重要性:
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謅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其道行,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忠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5]
元稹的奏疏再次強調:開通直言進諫的道路,拓廣接受意見的範圍,這是政治修明的基礎。元稹認為,君主如果能夠鼓勵、接受直言進諫,君子則願意為君主奉行他們的理想,小人也不做奸邪的事情,那樣君臣上下之意相通,幽遠之情可以暢達,天下怎能不政治修明呢!反之,君主如果抑制直言切諫的人士,因他們的直言切諫而懲罰他們,那樣君子就會藏身隱退,誠口不言,明哲保身。小人就會曲意迎合,從而竊取君子的地位,欺上瞞下的事情就會發生,那樣不招致禍亂是不可能的。
元稹的分析,辨證地指出君主納諫與否與正直之人和卑賤小人進退的關係以及與朝政治亂之間的關係,應該說對這一問題的論述是較為透徹的。元稹進一步批評了憲宗對納諫問題不夠重視。指出憲宗執政已有一年,沒有賞賜過進諫之臣,我們這些諫官曠年不曾被召見。以至於使不少諫臣每次上朝時,屏氣鞠躬,不藏仰視,這樣怎麼能議論朝政得失呢。供奉官(補闕、拾遺以上官為供奉官)尚且如此,更何況其它大臣呢。[6]
在上疏的最後,元稹就國事提出十條建議:(一)教導太子以崇重國儲;(二)任諸王以固磐石;(三)釋放宮人以消除水旱;(四)出嫁宗室之女以順應人倫;(五)經常召見宰臣以討論政事;(六)按職位序次召見臣下以增廣君主的聰明視聽;(七)、恢復正牙奏事制度以表明君主虛心求諫的誠意;(八)允許四方糾彈違法者以震攝奸佞;(九)禁止非正常的供獻以消除對百姓的無限徵求;(十)減少不時的畋獵遊幸以防止不測之患。在上事十條之中,(五)、(六)、(七)、(八)諸條都涉及到求諫納諫、擴大言路的問題。
元稹的數次上疏,是憲宗執政十五年中臣下最系統、最全面論述進諫納諫問題的章疏。當時即受到了憲宗的高度重視,此後憲宗經常召見元稹討論有關問題,元稹所提出的許多建議,憲宗也都很快地予以實施。
憲宗對求諫、納諫問題的重視,一方面是因為元稹等官員的督促,另一方面,主要是出自憲宗本人對太宗、玄宗貞觀、開元時代政治風氣的嚮往。憲宗既然要“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就必須主動地學習列祖列宗這方面的經驗。不過,由於元稹的上疏,促使憲宗將鼓勵直言進諫的問題及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自元和元年(806年)以後,憲宗多次在朝廷上鼓勵臣下要積極進諫,同時在制度上也恢復了正牙奏事制度,及時聽取諫臣們的意見。由於憲宗的高度重視,元和年間,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自貞觀、開元以來從未有過的良好的政治空氣。出現了像元稹、李絳、裴垍、裴度、白居易、呂元膺、盧坦、孔戣等一大批敢於堅持進諫的大臣,為元和中興打下了基礎。
其次,憲宗不僅重視求諫、納諫的問題,還特別強調臣下要敢於堅持正確的意見,敢於直言極諫。
憲宗曾對宰臣們談到,朕近來讀《貞觀政要》,看到太宗鼓勵臣下直言,不怕意見反復四、五次,感觸頗深。像太宗皇帝天資聰督,與群臣進諫者討論問題尚且如此,況且以朕之寡昧,如果簡單地處理進諫,難免不犯錯誤。憲宗因此規定,臣下上奏的諫言,不同意見可以上下往復十次。[7]
對於臣下強諫的問題,在朝廷大臣中也有不同意見,宰相李吉甫就堅決不主張強諫,他認為,與其使君臣各持己見爭論不休,不如在一定情況下順從君主,“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對此李絳堅決反對,認為:“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對此,憲宗明確肯定:“絳言是也。”為此,李吉甫抑鬱了許久。李絳歷來敢於陳述己見,表達不同觀點,時間稍久不諫,憲宗便會責備說:“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8]鼓勵李絳等大膽進諫。
元和三年(808年)四月,爆發了轟動一時的元和制舉案,憲宗親自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時,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前進士李宗閔都在策文中指陳時政之失,言語無所回避,吏部侍郎楊于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任考策官,策三人為上策,憲宗“亦嘉之”,[9]詔令中書省“優與安排”。
法門寺地宮典藏文物
三人的對策只有皇甫湜的對策文保留至今天,關於三人對策文批評的主要對象,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司馬光依據《舊唐書·李宗閔傳》所載李吉甫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10]罷考試官與復試官的記載,認為對策文所批評的主要是宰相李吉甫,並將這一觀點反映在《資治通鑒》中。
但是,據《舊唐書·李吉甫傳》及新書本傳記載,裴均曾在元和三年(808年)秋進言,認為李宗閔三人對策批評朝政乃是李吉甫的支使,也就是說,對策文攻擊的不僅不是李吉甫,而且是由李吉甫背後唆使的。
近幾十年來,一些學者根據現存的皇甫湜策文及文獻中“權幸”、“貴幸”一般所指的物件,認為元和制舉案中牛僧孺等所指斥的對象主要是宦官,而不是宰相李吉甫。[11]認為兩唐書李吉甫傳所載,乃是因為李德裕當政時,改撰《憲宗實錄》,曲為其父李吉甫隱惡。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元和制舉宰主要是發生在當權宰相李吉甫與應制舉人牛僧孺、李宗閔以及考策官之間的矛盾鬥爭。皇甫湜在對策文中所攻擊的是宦官專權,牛僧孺、李宗閔所指斥的則是宰相李吉甫。[12]
其實,李吉甫與宦官關係較為密切,李吉甫代表宦官泣訴於憲宗面前並不是沒有可能;憲宗是迫於宦官和宰相的共同壓力,才“不得已”將考試官罷免的。憲宗本人雖能容忍並嘉許對策文中的尖銳批評,但不能不考慮曾支持自己登上皇位的宦官的利益及宰相的感受,況且還有人指控主考官有營私舞弊的行為呢。
牛僧孺等人敢於大膽批評朝政,本身是與憲宗主張臣下應直言進諫,並在朝廷上下形成了一個敢於直言的大環境分不開的。
元和三年(808年)制舉案的發生,並沒有改變憲宗鼓勵臣下直言極諫的方針。為鼓勵大臣們直諫,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憲宗詔令京兆尹查訪貞觀著名諫臣魏徵的後代。當得知魏徵故居已被轉賣時,下令出內庫絹二百萬贖回,並厚賜魏徵子孫。[13]以此鼓勵臣下們直言。
元和五年(810年),翰林學士李絳曾當面向憲宗指責宦官吐突承璀過於專橫,主張應予以懲處。當時吐突承璀雖然指揮討伐成德失利,但恩寵不衰,因此憲宗發怒對李絳說:“卿言太過!”李繹泣對憲宗說:“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憲宗聽後解怒,對李絳說:“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14]
憲宗曾向給事中呂元膺詢問時政得失,呂元膺無所諱隱,辭氣激切,憲宗十分欣賞,第二日便向宰相建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元和四年(808年)征成德,憲宗擬授宦官吐突承璀招討處置使,呂元膺等八人聯合抗議,認為授宦官此職務不宜,憲宗於是改變了吐突承璀的使號。呂元膺擔任尚書左丞後,堅持原則,不拘私情,大膽進諫,曾多次將他認為不合適的詔命封還。曾有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卿王遂為營田之事爭持不下,憲宗懶於詳辨事非,將兩人都以美詞讚揚後改授它官。呂元膺接詔書後加以封還,認為事情應明示枉直,褒功懲過。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今江西贛縣)刺史李將順貪贓的情況,朝廷沒有認真複查,便將李將順貶為道州(今湖南道縣)司戶。呂元膺認為,無論裴堪所奏是否真實,朝廷都應按制度進行調查複驗。不加複驗將李將順貶滴,縱使裴堪所奏屬實,這種作法也不可為天下效法。於是呂元膺再次封還詔書,請憲宗派御史按問,查清事實後予以處理。[15]
給事中段平仲“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16]憲宗也予以鼓勵。御史中遠薛存誠也以敢於進諫、依法辦事而著稱。
對於那些身居要職,循默守位,不敢進諫的官員,憲宗總是毫不客氣地予以批評,甚至解除他們的職務。如鄭絪,憲宗登基前後,立有擁立功勞,元和初年與杜黃裳同為宰相,“謙默多無所事”,[17]從不提出規諫意見,因此被罷免了宰相。大臣權德輿也因諸事不肯表示意見、“拱默無建言”而被罷免。對於那些不但不上諫言,反而投君主所好,善於逢迎的人,憲宗尤為厭惡。元和四年(809年),宗正少卿李拭聞知憲宗準備以吐突承璀領軍討成德,因而上書請委吐突承璀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18]憲宗以李拭的奏狀出示群臣,並說李拭是奸臣,命令宰臣以後不要重用此人。
再次,憲宗不僅鼓勵臣下敢於直言極諫,而且自己注意納諫,集思廣益,隨時修正自己的過失。
憲宗一再強調進諫的重要性,但他並不是把勸諫當作一種點綴,當作一種擺設。而是真心實意地希望能夠集中臣下的集體智慧,群策群力,實現貞觀、開元局面的再現。因而在憲宗執政的大多數時間,都能虛心接受臣下的進諫,這是憲宗能在元和年間在各方面取得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然,作為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君主帝王,憲宗有著較強的自尊心,比較愛面子。所以當臣下的意見比較尖刻時,憲宗有時也會因難以下臺的窘迫而發怒。元和元年(806年)以後,由於憲宗的提倡和鼓勵,朝廷上敢於進諫的官員漸漸增多,有些諫言不但尖刻,有時還會與事實有出入。一段時間,憲宗十分惱怒。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憲宗曾對李絳說:“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聯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李絳回答:“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弊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19]憲宗聽後怒氣頓消。
元和三年(808年)七月,憲宗出行,視察秋稼長勢,隨行宦官將五坊的鷹、狗等狩獵用物一起帶上。一路上,遇有不少百姓觀望。第二天,許多諫官上書,認為秋日狩獵,損害莊稼,有損聖上愛民之心。憲宗十分生氣,上朝時對宰臣們說:朕昨日出行,實在是閱視秋稼,本非畋獵。今日諫官在外,章疏頗煩,不知意欲何為!
看到憲宗發怒,許多官員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此時宰相李吉甫上前進言:
陛下軫念黎元,親問禾黍,察閭裡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此則聖主優勤,天下幸甚。但以弧矢前驅,鷹犬在後,田野縱觀,見車從之盛,以為萬乘校獵,傳說必多。諫諍之臣,義當守職,既有聞見,理合上諫。拱默則懷屍素之慚,獻言又懼觸鱗之禍,果決以諫,實謂守官,正當嘉尚,非足致詰。夫蒐狩之制,古今不廢,必在三驅有節,無馳騁之危,戒銜橛之變。既不殄物,又不數行,則禮經所高,固非有害,然逐兔呼鷹,指顧之樂,忘危思險,易以溺人,故老氏譬之發狂,昔賢以為至誡。陛下每與臣等討論古昔,追蹤堯舜,固當棄常俗之末務;詠聖祖之格言;願以徇物為心,克己為慮,則升平可致,聖祚無疆,群臣異議,不禁自息。[20]
李吉甫的進言,一方面肯定了憲宗閱視莊稼,察民疾苦是正確的,同時又批評憲宗不應當以鷹犬隨行。既以鷹犬等狩獵用物隨行,有傳言天子狩獵便不足為怪。諫官既有所聞,便應盡職進諫。儘管事實有出入,也應當嘉獎鼓勵。李吉甫又指出蒐狩雖為古制,也應有所節制。天子應胸懷遠大,棄常俗之務,這樣傳聞就會不禁自消。李吉甫的進言,婉轉地對憲宗近來畋獵過多進行了批評,憲宗也認識到了自己的不對,連稱:“卿言是也,膚亦深悟矣”。[21]
在元和年間眾多的直臣中間,翰林學士白居易是較為突出並受到憲宗十分賞識的一個。白居易(772—846年),字樂天,太原人,生於鄭州。十五六歲時投文顧況,受到賞識。貞元十六年(800年)參加科舉考試,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參加制舉考試,列入第四等。初始任周至縣尉,集賢校理。從此以後,白居易大量規諷朝政的樂府詩篇,在宮內外廣泛流傳。憲宗讀了他的詩篇,不僅沒有因為白居易的許多直言而惱怒,反將白居易召入翰林院任命為翰林學士,以便於隨時聽取意見。白居易入翰林以後,“論執強鯁”,[22]曾經就元和三年(808年)制舉案、淮南節度使王鍔入相事、禁止諸道進奉、禁止掠良人為奴婢、中使監軍、元稹被辱、河北用兵等廣泛的問題向憲宗提出諫言,大多都為憲宗所接受。
法門寺地宮典藏文物
白居易的諫言,在許多時候往往比較直露而尖銳,有時白居易甚至直接與憲宗爭論,直言“陛下錯”,[23]使年輕的憲宗很下不了臺。元和五年(810年.)六月,憲宗曾因白居易的直言而密召宰相李繹入宮,對李絳說:“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李絳解釋道:“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24]聽了李絳的這番話,憲宗又高興起來,待白居易如初。
由於憲宗有納諫的誠意,因而元和年間(806—820年)敢於直言進諫的大臣層出不窮。給事中李藩在門下省,制敕有不合適的,即於詔書後批駁,辦事人員請以另紙書寫,李藩回答:那樣就成狀文,不是批敕了,[25]宰相裴垍十分賞識李藩的直言,向憲宗推薦李藩擔任了宰相,李藩任相後更是知無不言,深受憲宗器。元和中期,河東節度使王鍔用巨資賄賂宦官求任宰相,宦官請憲宗發密旨給李藩:“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李藩提筆將憲宗御批“兼”字“相”字塗去,使御旨成為“王鍔可宰”,並批敕曰“不可”。權德輿見之大驚失色:“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26]李藩回答:事情緊急,過了今日便不可改正,天已晚,何暇另外作奏章,於是封敕還上。
說李藩將御旨改為“王鍔可宰”,似乎言過其實,不過李藩駁回了憲宗擬以王鍔兼相的密旨卻是無疑。在李藩等大臣的反對下,憲宗放棄以王鍔兼相的打算。後來李藩雖不再任相,憲宗仍多次召對李藩,討論政事得失。
納諫的目的是為了改正過失,憲宗對此有著明確的認識,一般情況下都能接受大臣們的諫言,改正自己的過失。元和七年(812年),憲宗曾對宰臣們說:大凡行事,經常憂思的是不通於情理。一旦有了過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有何良法?李絳回答說,辦事情有過差,聖賢明哲也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天子應當經常用群臣來匡正自己的過失。主上用心治理於宮中,大臣討論匡正於朝廷。求治於天下未亂之時,消禍患於未萌之際。主上有過,則諫諍以制止,這樣上下同體,好像手足與心膂的關係,交互為用,這樣才能實現天下康寧。然而,這還只是一般的常理,亦非難以遵守之事。困難的是,當人主有了成績時,往往驕矝自滿,有了錯誤卻護短不肯承認,這是最易犯的錯誤,因此古人尤為重視有過必改,從善如流。聽了李絳這一番話後,憲宗立即答道:“朕擢用卿等,所欲冀直言,各宜盡心,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為慮也。”[27]
元和八年(813年),憲宗在接受李絳關於採擇宮女一事的諫言後,曾真誠地對宰臣們說:朕常居深宮,不知宮外的許多事情,以後如果有處理不當的事宜,你們必須像此事一樣論奏進諫,不要緘默不語,促成朕錯。如果朕得到你們的論奏,沒有採納,固執己見,而又有違於道理,你們直須兩度、三度進諫以至於更多。朕靠你們廣視聽、開茅塞,以歸於道理為目的,望你們能常以此為懷。
憲宗的一番話使李絳等宰臣深為感動,有的大臣竟淚流滿面,事後稱憲宗的勸諫、納諫,前無古人。“若書之帛簡,足以彰示萬世。豈尋常帝王可望清光哉。”[28]
由於憲宗注意求諫、納諫,聽取多方意見,善於集中集體智慧,因而在元和年間特別是元和初中期,能夠不斷地發現、糾正自己的失誤,最終實現平定藩鎮、再振大唐的奮鬥目標。
[1]《元稹集》第32卷,第36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標點本。
[2]《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30頁。
[3]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00頁。
[4] 《元稹集》第33卷,第378頁
[5] 《資治通鑒》第237卷,策7632頁。
[6]《資治通鑒》第237卷,策7632頁。
[7]《冊府元龜》第103卷,第1227頁。
[8]《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90頁。
[9]《資治通簽》第237卷,第7648頁。
[10]《資治通簽》第237卷,第7649頁。
[11] 岑仲勉《隋唐史》下冊,第43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唐長孺《山居存稿》第212—21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
[12] 程奇立《元和制舉案辯正》,載《煙臺師範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第37—41頁。
[13]《唐會要》第45卷,第810頁。
[14]《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82頁。
[15]《舊唐書》第154卷,第4104頁。
[16]《舊唐書》第105卷,第4089頁。
[17]《舊唐書》第109卷,第4181頁。
[18]《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60頁。
[19]《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6頁。
[20]《唐會要》第28卷,第530頁。
[21]《唐會要》第28卷,第531頁。
[22]《新唐書》第119卷,第4302頁。
[23]《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6頁。
[24]《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7頁。
[25]《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56頁。
[26]《舊唐書》第148卷,第4000頁。
[27]《唐會要》第52卷,第909頁。
[28]《李相國論事集》,第6卷,第50頁,《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法門寺地宮典藏文物
三、以史為鑒、堅持寬仁為本
善於向歷史學習,注意吸取歷史上特別是列祖、列宗的經驗教訓,這是憲宗元和執政的又一個特點。唐太宗時“以古為鏡以知興替”,吸取隋亡的教訓,終於出現貞觀之治的局面。憲宗早年學習詩書,對歷代的興亡原因也有所瞭解,即位以後,更是手不釋卷,經常閱讀《貞觀政要》及先祖《實錄》等書籍。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憲宗對宰相裴垍等大臣們說:“朕喜得人,聽政之暇,遍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辣慕不能釋卷。”又對裴垍等人說:“太宗之創業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臣與百官同心輔助,豈聯今日,獨能為治哉。事有乖宜,望卿盡力匡救。”[1]
這是憲宗從“貞觀之治”中學習太宗依靠群臣、共理天下的經驗。
對於開元、天寶之際,唐朝為什麼由盛轉衰,應吸取什麼教訓,憲宗也給予高度重視。
元和中期(809–814年),憲宗在延英殿與李絳等人討論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的得失,憲宗問李絳說:“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李絳為憲宗作了系統的回答:
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邱,嘗蒞官守,接時才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守泰,內外寧諡。開元二十年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嗜欲轉熾,國用不足,奸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奸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啟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消盡。甿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系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頤,鑒於化源,實天下幸甚。[2]
李絳為憲宗總結了玄宗開元、天寶治亂相反的歷史經驗教訓,從封建政治倫理的角度指出“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關鍵在於君主是否能夠依靠忠賢、去除奸佞,勵精聽納。
李絳所言,雖不能認識唐中期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的激化是導致唐中期社會變亂的主要原因這一事實,卻也從用人、勤政等方面總結了玄宗統治的經驗教訓,對憲宗是有借鑒意義的。“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3]成為憲宗隨時注意、君臣常常談起的問題,所謂“前事是今之高抬貴手,聯當自惕厲”。[4]
憲宗從列祖列宗的統治中吸取經驗教訓是多方面的。而討論最多的是治理天下的基本方針問題。這集中反映在元和六年(811年)三月,憲宗與大臣關於為政是以寬仁為先,還是以刑罰為先的討論中。當時憲宗徵求群臣意見,宰相權德輿綜合古今經驗,指出:
聖王設刑法,本以佐德,化期於無刑。仲尼有云,政寬則民慢;促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古人有雲: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聖賢折獄,眾疑之罪與五刑之疑皆赦。是以有流宥之典,有金贖之制,所貴導德齊禮,不務威刑。秦任法律,視人如草芥,及趙高原亥教以刑法,不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即位未幾,天下大潰。漢興,高祖除秦苛制,與人約法三章。文景二帝,恭儉愛人,始蠲去肉刑,惻隱之教洽於人心。當時風俗敦樸,公卿恥言人過,刑獄衰息。國家自高祖革隋,以寬代虐,及太宗文皇帝大聖至仁,見明堂圖始禁鞭背之制。列聖承遵,德厚成俗,是以雖天寶季年,大盜連起,以及建中,河溯悖亂,皆坐自擒滅,人心歸於本朝,此誠厚下感恩之所致也。[5]
權德輿以歷史上最負盛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與秦朝及隋朝的虐政相對照,說明執政應當以寬仁為本,以刑法佐之,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兩者結合,“政是以和”。對於權德輿的觀點,憲宗十分讚賞,他說:“朕嘗讀《貞觀政要》,見太宗文皇帝立言行事,動本至仁,當時四海欣戴,以致升平,後代雖有拒命之臣,不能動眾,實寬仁所致。誠符公等之言也。此即為政大本,當與公等同心務之。”[6]
憲宗從歷史上特別是從唐朝建國以來的統治經驗中得出一個結論,即為政寬仁,方能獲得民心,寬仁是“為政大本”,這是唐朝立國二百年,屢經變亂而復能存在的根本原因。由此,憲宗更加堅定了執行“寬仁”治國方針的決心。當然,憲宗實行“寬仁為本”的治國方針,並非始於元和六年(811年),只是經過這次討論,以寬仁為本的指導思想才更加明瞭。
對於憲宗的這一指導思想,朝臣們的見解並不是完全統一的,元和七年(812年)三月,李吉甫曾認為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憲宗即位以後,惠澤深而威刑末振,以致中外懈惰。李吉甫主張應“嚴以振之”。[7]憲宗徵求李絳意見,李絳認為: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之治,而效法秦始皇父子!憲宗對李絳的意見表示贊同。十幾天後,于頔上言,勸憲宗要峻刑酷法。憲宗因此對宰相們說,于頔是個大奸臣,他勸聯峻刑,是要使朕失去人心呀!
法門寺地宮典藏文物
其實,李吉甫關於賞罰不可偏廢的觀點並沒有過錯。李絳所說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也並不是不要刑法,只是以寬仁為主,以刑法為輔罷了。當然像于頔那樣公開勸憲宗要峻刑,顯然違背憲宗寬仁為本的主張,所以憲宗斥之為奸臣。通過憲宗的講話,可以看出,憲宗以寬仁為本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得民心”,憲宗清楚地認識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這正是他堅定不移地以寬仁之政作為立國之本的主要用心所在。
在元和年間(806—820年),憲宗總的執政方針是符合他的“以寬仁為本”的指導思想的,無論是改革朝政還是展開對藩鎮的討伐,都體現了這樣一種精神。
憲宗不僅注意從歷史上學習好的統治經驗,還十分注意吸取歷代特別是唐代以來前人及祖輩失敗的教訓。其中與臣下討論最多的,則是祖父德宗後期統治存在的一些弊端。
憲宗從童年到成年,經歷了祖父德宗整個的執政過程,對於祖父統治的得失有著一定的瞭解與認識。即位以後,曾一再總結祖父統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有意識地從中吸取有益於自己統治的教訓。如祖父晚年“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憲宗“心固非之”,[8]因而即位後選推宰相,推心委之,宰相得以各盡其才;德宗晚年多猜忌,朝廷官員們有互相往來過於親密的,都派禁軍加以監督,宰相亦不敢在家中會見客人,使君臣相疑,人人自危。憲宗則允許群臣的正常交往,君臣之間推心置腹,形成了良好的君臣關係;德宗晚年姑息方鎮,憲宗則堅持以法度制裁藩鎮。
在總結祖父統治的經驗教訓時,憲宗特別重視對涇師之變原因的探討。這集中反映在元和九年(814年)九月憲宗與李吉甫等人進行的一次長談之中。
涇師之變時,憲宗尚未成年,雖然對事件的經過仍有記憶,但對於涇師之變的深層原因卻缺少認識和瞭解。因而憲宗問李吉甫道:“朕頃在藩邱,嘗見侍讀言及建中歲末朱泚盜據宮闕,德宗皇帝播遷梁漢,累月艱危,鑾輿乃復,每用追憤,至今不忘。然未言賊臣兆亂之由,卿等詳記之否?”[9]於是,李吉甫為憲宗首先詳細地介紹了德宗執政初年孜孜不倦,勤於政事;多所建樹的事蹟,隨後指出德宗統治衰敗的過程與緣由,李吉甫總結四個原因:第一,賢相崔祐甫死後,德宗任人不當,使忠諫之言不得上聞;第二,小人乘機邀功,苟媚德宗,不顧實力主張全力討伐河朔。第三,當時討伐李希烈叛亂,京師民力物力已經耗盡,趙贊、陳京卻又在京師實行間架法(住宅按間數分等納稅)、除陌法(借商人資產),結果搞得中外沸騰,人懷怨怒。同時朝廷又征王公之家的奴僕馬匹以助軍。使公私囂然。第四,徵發涇原將士東討李希烈,而將士路過京師,卻不肯賞賜將士,又以粗糲飯萊相待,終於激發兵變。
李吉甫認為四個原因中,最主要的是由於輕易用兵和信任小人、刻剝百姓。李吉甫最後談到:“陛下為理,勵精深究理道,追念前朝之失,用為元龜,居安思危,實天下幸甚:”憲宗基本同意李吉甫的看法,但對於李吉甫稱德宗輕易用兵,似乎有所保留,憲宗認為涇師之變最重要的原因,是趙贊之法刻毒百姓,使朝廷失去了民心,損害了朝廷的寬仁之政。因此,憲宗連連稱趙贊、陳京是“賊臣”。[10]
憲宗還曾經與李吉甫談到德宗貞元中期以後,政事不理的原因。李吉甫認為,“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間養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憲宗則不完全同意李吉甫的意見:“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隨後,憲宗告誡李吉甫:“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11]
憲宗以德宗時宰臣懷祿偷安的事實,說明臣下也要對貞元中期的政事不理負責任,並以此告誡李吉甫等人,要敢於進諫,只有君臣共同用心,才能實現朝政大治。
[1]《唐會要》第53卷,第916頁。
[2]《舊唐書》第164卷,第4288-4299頁。
[3]《舊唐書》第15卷,第470頁。
[4]《李相國論事集》第6卷,第49頁。
[5]《冊府元龜》第104卷,第1241頁。
[6]《冊府元龜》第104卷,第1242頁。
[7]《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90頁。
[8]《資治通鑒》第53卷,第7654頁。
[9]《冊府元龜》第104卷,第1242頁。
[10]《冊府元龜》第104卷,第1243頁。
[11]《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90頁。
法門寺地宮典藏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