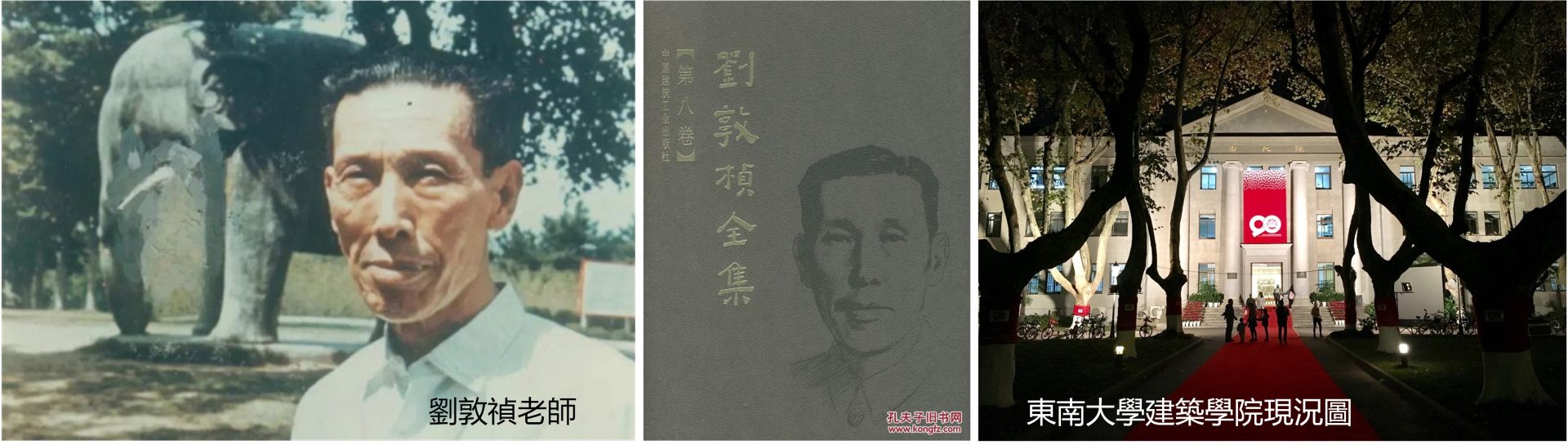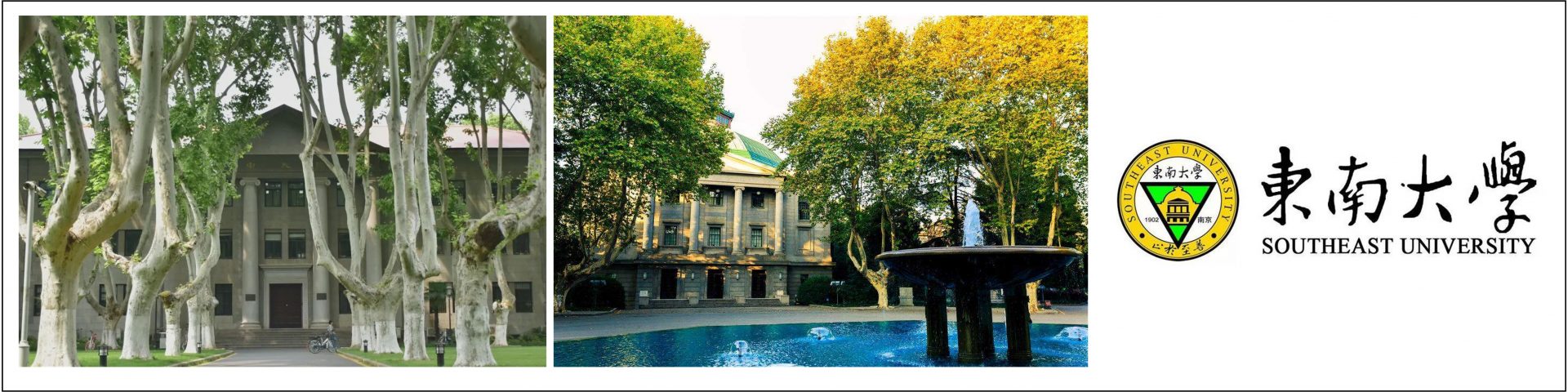山高水長—紀念劉敦楨先生
朱光亞
今年,2007年,是劉敦楨先生誕辰110周年。與一百一十年前的十九世紀相比,如今的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加速度發展的世紀,在新世紀頭幾年裡我們已感受到記憶體的增長總也趕不上資訊的爆炸,逼得我們把昨天還震撼的記憶在今天拋棄,把昨天熱銷的時尚今天就賣作廢品。然而,一旦我們離開現實的喧囂進入歷史,進入建築歷史與文化的圈子裡,進入中國近現代的建築學術發展史上,進入近現代建築教育的史冊中,劉敦楨的名字卻既無法隱去也無法繞過。歲月流逝,劉敦楨的話語依然回蕩在他工作過的東南大學的中大院中,劉敦楨的身影卻依然伴隨著,不,是依然引領著許多人的腳步。2000年,建工出版社出了一本反映近代四位著名建築界先驅的書,叫《建築四傑》,赫然第一位的即劉敦楨先生。
我生晚矣—走近劉敦楨和他的事業
劉敦楨,字士能,1897年生於湖南新寧劉氏家中,劉氏系大族,產生過曾任兩江總督劉坤一這樣的大人物,劉敦楨從私塾啟蒙,後赴長沙學堂讀書,1913年以官費生資格留學日本,再入東京工業學校(今東京工業大學),修建築科,1921年畢業,先後在日本和上海從事設計實踐,1923年與柳士英等人創辦了國內第一個由國人辦的中等專業學校的建築專業—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建築科,1927年應邀與劉福泰、李祖鴻等組建了中國第一個大學本科的建築系—中央大學建築系。1931年劉敦楨入朱啟鈐發起的以研究中國古代建築遺產為己任的中國營造學社,1932年他辭去教職,赴北平任學社文獻部主任,1937年抗戰爆發,劉敦楨與梁思成先生等一道,遷學社先至昆明再至四川南溪縣李莊,1943年在財政支持斷絕,學社極力支撐仍無法維繫時赴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再次任教,1944年繼鮑鼎先生之後任系主任,45年兼任工學院院長,後來劉敦楨先生組織學院回遷南京並辭去院長專任建築系系主任直到去世。
我是1978年因讀研究生才到南京工學院的,那時楊廷寶先生和童寯先生還健在,而劉敦楨先生已去世了十年。劉敦楨先生的追悼會是1978年才補開的,那是對文化革命的撥亂反正,追悼會是在大禮堂裡舉行,人頭攢動,挽幛上寫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是《詩經·小雅》裡的話,是司馬遷引以評價孔子的。在經過文化革命這場浩劫之後,我第一次看到一位知識份子被人們這樣評價,也忽然感受到了在經過萬馬齊喑的十年之後從沉默已久的人們心中發出的巨響。潘谷西先生帶著我參會,就如同去尋根認祖一樣,我不是本校的畢業生,所以潘先生向我介紹了劉老的情況,其實我在天津大學讀書時就已聽到老師們以見到學部委員劉敦楨和聆聽他的教誨為榮,但我自己則是被書本裡的劉敦楨觸動的。七十年代我好容易在一個省級圖書館裡托人借到了童寯先生著的《江南園林志》,在經歷了文化革命以及更長久的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歲月之後,讀此書時真有一種如醉如癡的感受,讀時一喜一驚,喜者該書通篇竟無一句應景的套話,在其自序中甚至有語曰:「吾國舊式園林,有減無增。著者每入名園,低逥唏噓,忘饑永日,不勝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吾人當其衰末之期,惟有愛護一草一椽,庶勿使時代狂瀾,一朝盡卷以去也。」[1]讀到如此醇厚的學術文章豈能不喜。可是,這話雖是寫於三十年代,拿到六十年代說無疑是自己跳出來準備當右派,而此老如此境界如此情趣何以不但沒有打成右派反能印出一部書來,讀之如何叫人不驚。我那時推測必定有奇人相助。再讀該書的序,作序者便是劉敦楨先生,序寫於一九六二年四月,文體一如童老先生,近於古文,直如舊時文人之唱和,劉敦楨說及名園更有「使遊者如觀黃公望富春山圖卷,佳山妙水,層出不窮,為之悠然神往」[2]句,可謂與童老心相通也,但內容似乎並無可以抓辮子的地方,說出書是為了修整舊園。讀序我始知劉敦楨先生推薦此書自三十年代始「由余介紹交中國營造學社刊行。。。。。。排印方始而盧溝橋戰事突發。。。。。。翌年夏,天津大水,寄存諸物悉沒洪流中。。。。。。一九五三年中國建築研究室成立。。。。。。因促著者於水跡蟲殘之餘,重新迻錄付印。」[3]據說當年建工出版社是要求童老改的,童老竟說一字不改,且要求印成了繁體字,六十年代中國有幾人得此待遇?六二年困難時期階級鬥爭放鬆是外部機遇,劉敦楨的支持無疑是促成此事的重要原因。
讀此書後不久,我就奔石頭城而來,不但在東南大學建築系的圖書館的借書卡上和古籍書庫的發黃的線裝書上得見劉敦楨的筆跡,更從前輩學人的言談身教和學術風格中走近了劉敦楨先生。我自認自己文字功夫尚可,但每見潘谷西先生在我的讀書報告和考察總結上的批語和對字詞及標點的改正即慚愧不已,始感東南學風源頭之清。我自認為自己邏輯思維應屬縝密,不料潘谷西先生幾次引劉敦楨先生語,曰:「孤例不足為證」。我耿耿於懷之外,從此不敢妄將推斷作結論。後讀劉敦楨先生論南京靈谷寺無樑殿文章,見劉老雖左右逢源,仍上下求索,最後結論仍然只說無樑殿是明代前期遺物但不能肯定是洪武年間構建,對「孤例不足為證」背後的精神始有所悟。潘谷西先生在教我園林建築屋頂鳥瞰準確的畫法的同時,也告知我當年劉老是如何要求南工的園林測繪圖做到準確優美的,我才知道中國最出色的園林測繪圖上是如何積累了兩代人的努力和一種共同的學風的。
我自出校門,命運所驅,在建築專業中摸爬滾打整整十年後回身校園,自會有自己的學術見解,深感建築是實踐科學,我服膺者是那些坐而論道且起而行道之人,從潘谷西先生學習園林,苦於自己以往知識體系無法把握疊山設計及施工之技,潘師介紹劉敦楨先生當年瞻園南假山的創作經過,說是劉敦楨教授、彭沖書記,疊山匠師王師傅三位共同商量以三結合的方式完成。我深感興趣,前往瞻園,見南假山之洞壑幽深,山徑曲折,更有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我見所未見,那境界不正是童、劉二老在江南園林志中所追求的嗎,驚歎之餘,我亦悲亦喜,悲者,我生晚矣,我覺晚矣,喜者,譬如遊子,在浪跡天涯之後,回歸故里,這與杏花春雨相伴的江南,這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劉敦楨為《江南園林志》所作序中所說的一九五三年中國建築研究室的建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繼營造學社之後的又一次重要的學術研究機構的經營,它是建工部出資,劉敦楨組織領導的附設於南京工學院的研究機構。在「糞土當年萬戶侯」為是,「厚古薄今」為非的時代大氣候中,它的成立純屬另一個偶然機遇—應正在編百科全書的蘇聯科學院之邀撰寫中國古代建築簡史,中國建築研究室及與之相隨的南京工學院建築史研究雖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十餘年,且一次次的被無情的政治運動威脅和摧殘,但仍然完成了《中國古代建築史》,《蘇州古典園林》,《中國住宅概說》,《徽州明代住宅》這些代表了整個中國五六十年代建築史學界研究成果的著作或初稿,培養和造就了中國建築史界第二代的的傅熹年、潘谷西、郭湖生、王世仁等幾位領軍人物和更多的建築界的棟樑之材。他們每人談起的往事中都能發現劉敦楨的光澤。記得國家文物局的朱希元同志說到劉敦楨的一次園林講課,當時劉敦楨六十年代用人的眼、耳、鼻、舌、身走近園林後的感受解說園林藝術的要點,這其實不就是西方的建築行為學和建築心理學的統一嗎。可在劉敦楨的園林著作中沒有說及。怪不得他的學生們說他上課拿起一杯茶侃侃而談就讓你永難忘懷。
宗廟之美—認識劉敦楨在學術上的貢獻
《論語。子張第十九》有「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是有了各地孔廟上對孔老夫子稱頌的「萬仞宮牆」的標準匾額。宮牆雖高,萬仞卻是誇張之語,否則儒學何以能傳承下來。但對於初學者來說,入得宮牆,認識前輩的學術貢獻又確實困難,沒有一定的學術積累難以和前輩對話,得窺宗廟之美談何容易。我對於劉敦楨的思想境界早已心儀,但對他的具體學術貢獻則是隨著改革開放後的學術發展及自己的研究深入和積累增多後才逐漸認識的。記得八十年代初讀郭湖生先生紀念劉敦楨的文章,文中說及營造學社在吸納了梁思成劉敦楨兩位歸國人才之後研究成果發生了質的變化,有「如出硎新刃,銳不可當,使一切作皮相之談者為之瞠目」[4]一句。我既有感於郭先生文字的犀利,又第一次認識到梁思成、劉敦楨在學社期間的劃時代的貢獻。讀《營造學社彙刊》就會知道,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現代的建築學的實證式本體考察及精確性圖學研究與清代以來的考據學相結合,奠定了中國現代的建築史學學科發展的基礎,其最著名的成果可以梁、劉二人合寫的《大同古建築考察報告》為代表。圖文之外,還有以量化的分析論及斗拱的演變。
劉敦楨一生中留下的最顯著的貢獻即是《中國古代建築史》的編撰,該書扉頁印有「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史編委會組織編寫,劉敦楨主編」兩行字,接著有說明,提到,「1959年建築科學研究院理論及歷史研究室組織了中國建築史編輯委員會,開始編寫《中國古代建築史》」,歷時七年,前後修改八次。應該說,這是一份集體研究的成果,是一部集體的創作。劉敦楨同志從開始到成稿主持了編寫工作,發揚了嚴謹認真的學風,付出了不少的精力和心血。梁思成同志參加了編委會的領導,也是第六次稿本的主編之一,並在1965年主持了最後一稿的審定,對本書的編寫起了積極的作用。。。。。。」[5]四十年多前的那種工作模式:黨的領導,群眾路線,三結合等恐今日的中年以下者皆已不知,書後的說明詳細列出了參加工作的人員名單,梁劉之外,自部長以下有名字的五十二人,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建築史學界的幾乎所有精英都參與了這項工作,可以說它是當時的一項國家性的文化工程。說明的落款是1978年3月,此時梁公離世已經六年,劉公則已離世十年了。此時也是文革雖已結束、三中全會尚未召開之際,文字謹慎,並加提防式說明:「雖力圖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總結各個歷史時期建築發展的過程和規律,但仍感有不足之處;全書偏重於記敘,對於源流變遷的論述還不夠;對建築的藝術方面比較側重,對建築的技術方面則注意不夠。。。。。。」[6]就算有這些不足,今日看來該書至少有如下貢獻:第一,它是第一本中國建築史界認可的代表了當時國家和民族整體研究成果水準的中國古代建築歷史著作;第二,它是第一本較此前任何著作都更為充分地反映六十年代為止的全國各地各民族建築遺存及考古發現成果的全面、系統的建築史學著作,它為此後的其他著作和其他闡釋提供了基本的資料平臺和歷史框架;第三,它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觀和嚴格審慎的學風從宏觀上提煉與歸納了中國建築發展脈絡和特點,又以翔實的案例和高品質的插圖闡釋了中國建築的基本形制、藝術和技術成就的著作。因此,它是自營造學社開始至六十年代為止的中國建築史學成果的大結集,是那個時代的里程碑。至於那些問題以及雖未列出以今日觀之也存在的問題,有些本來就是那個時代的必然產物,有些則尚待時日才能解決。又一個三十年過去,五卷本的中國古代建築史由第二代建築史家推出,中國建築技術史和中國建築藝術史也出版了,此時已是二十一世紀了,某些方面的問題後人仍未完全解決,何能苛求於前人呢。
劉敦楨另兩個突出的貢獻在園林和住宅的研究。劉敦楨對園林的興趣可追溯至二、三十年代他在蘇州工專和四十年代重返南京的日子,楊廷寶和童寯二人1978年在為劉敦楨的《蘇州古典園林》作的序中即談到「早在三十年前,他就是研究園林藝術的少數人之一」[7]可能即是指的這其中的一段時間。1956年劉敦楨在南京作《蘇州的園林》研究的學術報告,揭開了全面研究江南園林的序幕,並帶動了其他學者的研究興趣。其最後書稿是文化革命以後由潘谷西等先生整理成的。該書如楊、童二老序言所云「是在他主持下,多年研究的結晶,對我國園林藝術精極剖析,所論雖僅及蘇州諸園,然實中國歷代造園史之總結。」[8]劉敦楨對住宅的研究始於抗戰期間的逃難路上和在雲貴川的學社調查中,連同回新寧老家也沒有忘記測下平面圖來。這些成果經整理於1956年完成為《中國住宅概說》的書稿,次年由建工出版社出版。1952年他帶隊赴皖南調查民居,初步成果在1953年的文物參考資料上發表,同年他擔任主任的中國建築研究室開始了全國民居調查。六十年代由他作序的《徽州明代住宅》出版。以今日的眼光看待這兩個領域的成果,我們對劉敦楨五六十年代的多產並不太驚訝,因為他積累豐厚又把別人消遣的時間都用在了寫作上。使我們驚訝的是劉敦楨先生何以比他同時代以至後代的人更早地關注這兩類民間建築,是什麼賦予了他這種眼界。要知道就世界範圍而言,只是到了二戰之後,隨著歐洲中心論的思想被新的文化多元論潮流所代替,人們才開始關注那些哺育了主流文化的民間文化的遺存。21世紀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民間建築文化是地區和民族文化基因的寶庫。抗戰時的劉敦楨對民居的關注至少說明了劉敦楨的心一向是貼近平民的。與此類似的是他對印度等亞洲國家建築的關心,可惜他沒有來得及展開東亞建築史的研究就在文化革命中去世。
老中央大學被比作中國建築教育的老母雞,因為不僅新中國的眾多建築界的棟樑之材來自該校,且眾多的建築院校的老教師也是中大畢業生。多數院校的辦學理路和血脈可追溯至美國賓州大學等校和更早的學術源頭巴黎藝術學院,因此被戲稱為學院派,其實不確。每個學校都面臨著自己調整的任務,由鮑鼎和劉敦楨在抗戰中的重慶主持的中大建築系被學生稱為沙坪壩黃金時代,充滿了感人的回憶,也有著明確的學術定位和指導思想。總體要求是以高品質的綜合素質訓練培養學生,適應中國的建築市場需求。從多位中大學生的回憶錄中可以知道,以鮑鼎、劉敦楨為代表的老中大的教授梯隊的建築教育安排至少有以下一些特點:一是相容並蓄,吸納了不同背景的建築界精英,最引人驕傲的是沙坪壩時代在工學院長盧孝侯先生的支持下,先後將建築界的四大名旦(楊廷寶、童寯、李惠伯、陸謙受)請進中大兼職。二是注重實際,劉敦楨本人有著堅實的技術學科基礎和從業建築師的經歷,早期中大建築系的課程安排就包含了數門力學在內的技術課程,中國最早的學生古建築考察就是1931年由他在中大帶隊進行的。中大教授多有事務所經歷,以實際經驗把握教學不致遁入空門。唐璞先生的回憶錄中介紹了沙坪壩時代他自己的形式主義設計如何受批敗給了注重功能的張鎛的設計的[9]。三是創造小環境,中大前期就注重購置圖書,製作模型。吳良鏞先生用「烽火連天,弦歌不輟」八個字概括抗戰艱苦環境下,甚至在警報頻仍紙張難覓的環境中,中大學生依然享受著和大師對話交流的高品質的教學[10]。四是嚴格要求,言傳身教,在建築系的大圖房中,先生們改過同學的設計圖後要求第二次交的圖作出改進,有同學沒改好,譚垣先生就將學生罵哭了。到了交圖的日期和時間,劉敦楨會親自帶著助教來裁圖,一點也不得拖延[11]。而教師們的嚴於律己,獻身教學的精神也十分感人,甚至如楊廷寶、李惠伯等人自己拿錢設獎鼓勵學生學習知識技能。[12]五十年代以後,院系調整和「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為整個教育搭起了新的構架,但在這新的構架中,老的傳統依靠幾代學者的積累和傳承依然在發揮作用。
山高水長—尋覓劉敦楨的心跡
在《中國古代建築史》書後的編寫說明中有一段話:「1960年7月經劉敦楨教授修訂後完成了第二稿,並在北京召開的建築史學術討論會上進行了討論。根據討論意見,於1960年9月修訂為第三稿,約13萬字。參加修訂工作的有同濟大學陳從周、喻維國,西安冶金建築學院趙立瀛,文化部文物局陳明達。。。。。。」[13]今人讀後會想,怎麼劉老先生老也改不好呢?雖然韓愈說過「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可今天我們還是無法想像學生們被賦予了何種勇氣去改老師修訂好的稿子的,老師們又是何種心態去接受學生的改寫的。原來,當年為了改造大部分作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老教授們,學生們被鼓勵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批評老師,用毛澤東的話說,三娘教子之外,還要「子教三娘」,教的方式自然包括批評與修改文章。劉敦楨自然不會例外,但互教互學卻並不都是鬥爭。好在三十多年後,喻維國和他的夫人、曾在東大任教的張雅青女士共同從美國寄回一篇回憶文章中多少提到了這件事:「1960年夏,維國前往北京參加中國建築史學術會議,第一次見到劉老。那時劉老客居在建築科學研究院大樓的西翼,一個簡樸的房間裡。。。。。。他廢寢忘食地在這裡專注於寫作。之後,維國有機會多次在劉老指導下學習工作直到1966年初,一切應該進行的工作都必須停下來時為止。」[14]文章還提到「1965年下半年我在南工參加中建史教材的編寫。一天下午突然有人叫我聽電話,。。。。。。只聽到『我是劉敦楨』,我頓時的反應,一定有什麼緊急的事,正想發問,劉先生說:『下午四點鐘到我家來一趟,我家做了些菜,你拿去大家嘗嘗。』這時我的心情從緊張馬上轉到愉悅……」[15]文章最後憶道,「往事在腦海裡翻騰,不禁熱淚縱橫難以自己……還是讓我們放聲歌唱:……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東南精神,山高水長」[16]兩代人之間的實際關係竟是如此感人。原來學生們是在劉老的指導下以學習的態度完成修改任務的。山高水長是他們對劉敦楨先生楊廷寶先生等的精神狀態的概括,本文也就借此去尋覓劉敦楨的心跡。
劉敦楨少年時到省城讀書,接著十六歲負笈東瀛,包括他棄機械而轉入建築的學習選擇都既是歷史機遇和自己的努力也是家庭推動的結果。而在1922年回國後的學習與謀生之路上,尤其是1932年他放棄中央大學教職任營造學社文獻部主任之後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六年中,我們看到的是在風雲激蕩的大格局中一個典型的優秀中國知識份子的人生軌跡和深沉的價值取向。中大建築系副教授的工作顯然很適合劉敦楨。第二年他就在《科學》雜誌上發了《佛教對中國建築之影響》,接著入營造學社和不斷在學社彙刊上發文。但當朱啟鈐要他和梁思成加盟學社專職工作後,他放棄了較優裕的待遇和南方生活方式北上,投入了古建築考察和研究中,他心中顯然有一種夢,這夢比不習慣的生活更重要,這夢曾經激勵了梁思成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完成了中國唐代建築「佛光寺」的發現和考察,這夢也激勵了劉敦楨在盧溝橋事變前完成了至少二十篇考察報告和論文。梁、劉二公皆為俊傑,梁公出身名門,文風奔放,劉公嚴謹深沉,文章擲地有聲,數十年後後人結合地緣格局及譜系參照需求以「南劉北梁」稱之。我不知當年二公相遇是何感覺,但林宣先生,這位既是梁夫人林徽因的本家,又是在東北大學和中央大學兩校學習過因而是梁、劉二人的雙料學生的學者,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及一段趣事,說當時有一段佳話流傳,說梁、劉二人第一次相見,討論中國建築研究如何著手,兩人分別在紙上寫字,拿出對照,不約而同是「材、栔」二字[17],若果真如此,不知二人是否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覺。但顯然兩人瑜、亮都不是,從當時及後來的歷史來看,兩人有過一篇合作之文,即《大同古建築考察報告》,其餘皆各自寫成。在學社困難的大西南時期,梁、劉仍堅持維繫學社,為省經費,劉敦楨還兼職會計,加上林徽因和當時還年輕的劉致平、莫宗江、羅哲文、陳明達堅守著學社陣地直到經費完全斷絕,劉敦楨和陳明達於1943年離去,1944年學社宣告解散。五十年代公開批梁思成復古主義時,劉敦楨的會議發言也仍以朋友相稱,即使在後來六十年代劉氏主編,梁氏主審古代史的時期,亦未見他們有過齟齬,據現可看到的劉敦楨寫給傅熹年的多封工作信件中,當時梁劉二位學者之間既有對問題的切磋琢磨,如對佛光寺彌陀殿的討論[18],也有在新的階級鬥爭和官本位形勢下的各自和互動的調整[19],對照劉敦楨和楊廷寶、童寯那種後來多年共事互相信任也仍是平常並無來往應酬的關係,即知幾位建築界前輩學者包括梁、劉間其實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何況經歷了反右鬥爭。
1949年的政權更迭改變了中國大陸的生產關係,也改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改變了建築師和一切知識份子的定位。劉敦楨和楊廷寶、童寯都自願留下來,經歷了鎮反、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運動,看到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喜悅,也看到了改變了的生存格局,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調整了自己,我相信作為系主任和研究室主任的劉敦楨的調整是最大的,作用也是最大的,它為一批人提供了一定的話語權、知情權和參與權,除了本文開頭說及的《江南園林志》的出版外,如果比較一下幾個院校在反右派和文化革命中的損失,我相信南工是最小的,雖然劉敦楨本人在第二場運動中也被波及並於1968年因病不治過早去世,但畢竟,南工建築系的古建模型沒有被燒掉,批鬥中沒有人自殺,期刊室的外文期刊沒有燒掉且得到了續訂,甚至工宣隊進校了要撤掉建築系童老還可以放一次厥詞[20],這當然首先是學校沒有在天子腳下的緣故,但幾十年來以劉敦楨為首形成的師生間的和諧人際關係、中庸傳統和對政治的謹慎作風的影響是那場運動的緩衝器。
根據現在披露的材料看,劉敦楨在主編《中國古代建築史》這項里程碑式的工作中一點都不讓人羡慕,八稿中第一稿只用了六個月,而二至八稿用了六年。編寫者面對著一對永難解開的冤家,即統治階級的腐朽和勞動人民的智慧,它們之間的階級鬥爭構成全部歷史。唯物論本是一件思想的利器,但集體創作領導審批中的各個好漢咸淡口味並不相同,這使得劉敦楨工作中的精益求精,從善如流的學風和加鹽加水的需要攪在了一起,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或者是幾個夾縫中忍辱負重的苦行者,在完成八次修改探討數百上千個問題和注釋的過程後,他們始終未找到階級鬥爭的鹹淡的恰當表達法,劉敦楨說:「梁先生曾要我不搬用階級鬥爭。。。。。。等生硬的名詞,而能使讀者不知不覺中感覺是用階級觀點寫的。我在六、七、八稿中都作了一些嘗試,無奈我的水準很低,達不到這個標準,想來想去,與其畫虎不成,不如老老實實搬用一些成語,反為妥當。。。。。。請您轉請汪、劉二主任代為見證為幸。。。。。。」但後來還是繼續改了。我們看到集體研究的參加者的發言談及每次開會都有收穫,都有東西帶回去,甚至成為教學中的資本,也看到編寫者偶爾的喜悅和回饋的肯定意見,看到書後提及的鑒定會通過的結論,但顯然最後的重要的評價意見是「史稿在緒論內籠統批判,而以後各章具體事例都說是好的」即抽象批判,具體肯定,厚古薄今,能否出版不得而知[21]。劉敦楨後來在給傅熹年的信中再次提及:「我們的水準不高。」提到:「有人說劉先生這大年紀,尚且摔了跤,丟了面子」,然而他仍說:「從個人得失出發,確實是丟面子,但從嚴肅的任務來看問題,就無所謂面子不面子了。。。。。。現在我除努力完成任務以外,什麼也不考慮。」「中國建築史總是要寫的,事物的發展總是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的,我們既然幹了就應該幹到底」、「世界上沒有一本任何人都同意的書,批評意見只要對工作有利,就應該虛心接受」[22]他開始了第九稿的修改,他刻了一方「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印章,用以自勉和勉勵傅熹年和王世仁等人。在第八稿中,他不寫序,只寫了編輯經過,一一列出了參加修改工作和審稿工作的別人的名字。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情懷,何等的堅忍。我們應該慶幸,劉敦楨和他的同志,用他們的堅忍,包裹起心血和淚水,承擔起誤解、冤屈和犧牲,挾裹著時代的泥沙完成了歷史對他們的託付,我們才有了里程碑。
任何學者都無法完全擺脫他對時代的影響,任何學者都要面對他的時代的問題。劉敦楨的最重要的學術活動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大陸確立到爆發文化革命的歷史性新變局中。離開了對這種背景的瞭解無法認識劉敦楨等一批中國建築界學術先驅的貢獻和精神。當救亡壓倒啟蒙,當一切舊制度的污泥濁水看起來終於被中國革命所滌蕩,一個嶄新的中國屹立於世界東方之時,革命在征服了中國大陸的同時也征服了中國的知識份子,以新中國為實證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它鮮活的魅力成為知識份子努力構建理想的新框架。在半軍事化的節衣縮食後的成功建設面前,人們知道了每個人都要以一定的犧牲為代價。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但在犧牲之後。所以我們看到了知識階層的優秀分子,即使被批,被打成右派也仍然願意反省自己擁護繼續成功。站在歷史的高度看,1957年前前後後的運動中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中的多數都是政治的未成年人,犧牲了他們的幼稚和真誠,運動進而導致思想界和學術界思維自由的犧牲。此後建築史學介面對著以唯物史觀代替人類思想遺產,又以階級鬥爭代替唯物史觀,缺少武器的批判卻充滿了批判的武器的環境,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以嶄新的形式出現,此時的「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今天看來後果可知,而當時則是任務、責任、危險、挑戰都重疊在一起。或者是歷史的安排,命運的驅使,劉敦楨置身這環境的靶心,他的永不言棄的信念應對了這種環境,完成了普羅米修士似的奉獻。
今天的建築史學界以及整個建築界都面臨著新時代的新問題和老時代留下的老問題,我們不必停止在前人的思想成果前而是面對和解決好自己時代的問題,我們不應苛求前人而是剖析歷史汲取教訓避開歷史的輪回,在這過程中,劉敦楨先生為我們留下的學術遺產和精神遺產值得珍視。
謹以此文紀念逝去的劉敦楨先生。
[1] 童寯《江南園林志》自序。
[2] 童寯《江南園林志》,劉敦楨序。
[3] 同上。
[4] 郭湖生《憶士能師》,載《建築史》77期
[5] 《中國古代建築史》建築工業出版社。
[6] 同上。
[7] 楊廷寶、童寯《<蘇州古典園林>序》,建築工業出版社,1979年。
[8] 同上。
[9] 唐璞《春風化雨憶當年》,載《東南大學建築系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專集》,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97年。
[10] 吳良鏞《烽火連天,弦歌不輟》,載《東南大學建築系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專集》,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97年。
[11] 張致中,《建築系的大繪圖房》, 載《東南大學建築系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專集》,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97年。
[12] 見 吳良鏞《烽火連天,弦歌不綴》 及劉光華《回憶建築系的沙坪壩時代》,載《東南大學建築系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專集》,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97年。
[13] 《中國古代建築史》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422頁,《中國古代建築史》的編寫過程,1984年,第二版。
[14] 張雅青,喻維國《山高水長》,載《東南大學建築系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專集》,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5] 同上。
[16] 同上。
[17] 林宣《我在中央大學建築系三年的學習生活》 載《東南大學建築系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專集》,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97年。
[18] 天津大學博士論文〈中國建築史學史初探〉附錄,《劉敦楨致傅熹年信第十九》。
[19] 六十年代南京工學院與建工部合辦的建築研究室與北京的建築研究室合併,梁思成任主任,劉敦楨任副主任及南京分室主任,研究室設在建設部建築設計研究院,院長為汪之力。
[20] 據建築研究所的教師說,當時工宣隊因建築學專業滋生資產階級情調,建議撤銷併入土木系,徵求童寯意見,童寯的回答是:「不可,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21] 同注18,《劉敦楨致王世仁、傅熹年信第三十》。
[22] 同注18,《劉敦楨致王世仁、傅熹年信件第三十五》。